悦读九江丨向水而生:县城写作的根脉与呼吸
向水而生:县城写作的根脉与呼吸
□ 晏子
关于县城写作,我深有体会。我的写作,大抵是离不开水的。
我的共青城,离湖只需一刻钟车程。南湖大桥如一道飞虹,连接着县城的烟火与大学城的书卷。桥上有公交往返,桥下有垂钓者悠然自得。岸边矗立商业写字楼和高档小区,还有移民建镇的安置房。禁渔期,渔民不能下湖捕捞,但他们每天都会来到水边,在湖滩上走一走,看风中摇曳生姿的芦苇,看越冬的候鸟在浅水里嬉戏。忆当年渔歌唱晚的火热场景,他们感慨万分,目光中流露出沧桑和深深的眷恋。
这里每天都发生很多故事,他们成为我笔下的素材,于是我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了《娘山》《倦湖》《喊湖》《奶奶的月牙船》《龟山有龙》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有位老师说:你是江西唯一的一位笔始终贴着湖岸走的作家。是的,我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大湖,包括长篇纪实小说《巴望河》,虽然写的是越战故事,但主人公是庐山脚下的鄱阳湖人,有很多关于他青少年和荣归故里后,对鄱阳湖场景的大篇幅描写。我是渔民后代,我的笔离不开大湖的一草一木,离不开鱼水情,离不开在风口浪尖上求生的渔家儿女。
以发表在《芒种》的中篇小说《向水而生》为例。这篇小说始终围绕着水来展开人物的命运。马敦、陈晓霞像湖里的鱼,一旦离开了水,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即便在北方的城市立住了脚,还混得不错,但最终一败涂地,拖着奄奄一息的残躯回到大湖。在落入水中的那一刻,他麻木的身体似乎有了知觉,有了召唤,有了意识和复苏。尽管他在离开家乡的时候,做了愧对江东父老的事,但大湖人不计前嫌,无私地包容、接纳并拯救了他,把上善若水的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
常有人问,鄱阳湖的故事,是否已被你写尽?我答,不可能。湖的生命力在于其生生不息,岸上人的坚韧、勇敢,便是故事不竭的源头。若说前期的作品,我更多是在描绘大湖的“容颜”与“心跳”,那么在新的探索中,我渴望能潜入更深层的水域,去寻觅它的“根”与“魂”,探索它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从而上升到生命的尊严、乡村权利结构、家庭伦理和乡村空心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这便是我理解的“县城写作”。它并非一种题材的局限,而是一种根系的深扎。它要求我们不仅是地域风貌的记录员,更是这方水土孕育的独特伦理、情感方式乃至命运逻辑的勘探者。
我起步较晚,写作之路犹如一叶扁舟,在省作协师长们的护佑下,于文学的湖面上缓缓撑篙。这是一个需要与时俱进的时代,我常感压力,却也深知,一个写作者的使命,便是逼着自己往生活的深处、人性的幽微处前行。能走多远,是能力之事;但方向,必将始终朝向那片养育我的浩渺之水。
只因那里,有我最深的根,和最沉的呼吸。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文婧
责编:肖文翔
审核:朱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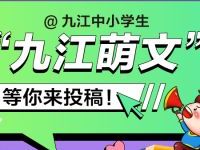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