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岁月丨当爱让生命重新呼吸
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动,那冰冷的滴答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剐着我的心。我握着母亲的手,那曾经为我纳过千层底、缝补过无数衣衫的手,此刻却布满暗红色的针眼,像一串被命运强行穿上的血色佛珠。三天了,医生已经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每一次签字,钢笔都在我颤抖的指间打滑,泪水模糊了“同意”那几个沉重的字迹。
“带她回老家吧。”主治医师摘下口罩,疲惫的皱纹里藏着不忍,“让老人……叶落归根。”这句话像一根刺,狠狠扎进我心里。我知道,这是医生最后的仁慈。
三年前的八月,母亲从安徽枞阳老家来到彭泽我家小住。八十二岁的她腰板还算硬朗,总抢着洗衣服、做饭,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闲不住。我劝她歇着,她就笑着说:“做惯啦,歇着反而不自在。”本想让母亲在我这里享享清福,感受一下县城的生活,避免在老家乡下的孤单,谁能想到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差点夺走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阳光。
那是一个寻常的清晨,母亲起床后就说有些头晕,我并未太过在意,只当是她夜里没睡好。可到下午,母亲开始上吐下泻,到傍晚整个人虚脱得都站不稳,我才惊觉大事不妙。120的警笛声穿透黄昏,在救护车蓝光的闪烁中,我看见母亲苍白的脸贴在担架上,像一片即将飘落的枯叶。
在普通病房住了一天一晚,打针吃药,病情不见好转。经过检查,肾脏器官开始出现衰竭现象。随即,母亲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ICU的玻璃门成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屏障。我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看着母亲身上插满管子,呼吸面罩下的胸膛微弱起伏。每天十五分钟的探视时间,我都要把攒了一整天的话说完,却总在开口时哽咽。第三天夜里,主治医师把我叫到走廊,白大褂在荧光灯下格外刺眼:“肾脏衰竭……做好心理准备……”后面的话都化作了耳鸣。
此后,听到医生每一次病危通知的冰冷话语,我的双腿都忍不住发软。药物、仪器全力运转,却依旧阻挡不了母亲病情的恶化。医生遗憾地宣告救助无望,建议将母亲送回老家,或许熟悉的环境能让她最后的时光更安宁些。我死死攥着病历本,纸张在掌心皱成一团。联系救护车送老家的过程也较艰难,疫情期间,彭泽县人民医院所有救护车辆都在超负荷运转。最终还是老家那边医院答应派来救护车,我反复叮嘱要带医生、带氧气,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
启程那天晨雾浓重,亲友们红着眼眶站在路边,像在举行一场沉默的告别仪式。救护车里,母亲的气息轻得几乎察觉不到,我握着她的手,生怕一松开就会消散。车窗外,熟悉的街景飞速后退,就像我的童年、我的青春,都在这一刻被疾驰的车轮碾成碎片。
老家门前的老槐树依旧郁郁葱葱,可树下再没有那个踮脚张望的身影。看到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邻里们叹息着摇头,几个长辈都建议我们兄弟为母亲准备后事。不多久。丧葬用品就堆满了屋子,刺眼的白色裱纸犹如提前降下的雪。停药的母亲安静得像一尊雕像,只有偶尔的呼吸证明时间仍在流动。我和兄弟们轮流为母亲擦身、换尿布,在每一次触碰中都祈祷能感受到体温的回暖。
第五天黎明,一缕阳光穿过窗棂时,母亲的手指突然动了动。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封的河面裂开第一道缝隙。她缓缓睁开的眼睛里,映着我们泪流满面的脸。“妈……”我唤得小心翼翼,生怕惊醒了这个易碎的梦。当她艰难地咽下第一口米汤时,滚烫的泪滴在碗沿,溅起微小的希望。
康复的过程像一场温柔的奇迹。母亲先是能靠着床头坐一会儿,后来竟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
今年清明,她非要去给父亲上坟,在坟前说了好久的话。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我忽然想起她四十多岁守寡时的样子——那个瘦小的身影,硬是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了四个儿子的天空。
这几年每次回老家,刚下车就能听见她中气十足的呼唤。她依旧爱操心,尤其惦记长孙的婚事。“别太挑了,”她总这么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担忧,“我啊,就想活着看见重孙子……”这话让我鼻酸,三年前那场病后,她的每分每秒都是上天额外的恩赐。
前些日子陪她晒太阳,她突然说起我小时候发烧的事:“你烧得说胡话,我就整夜抱着你在堂屋转圈……”阳光在她银发上跳跃,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奇迹,不过是母亲用爱创造的日常。就像现在,她粗糙的手掌抚过我额头的感觉,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轻轻摩挲着手机里母亲的照片,她笑得那么满足,仿佛历经的苦难都化作了皱纹里的阳光。这个用一生诠释坚韧的女人,教会我最重要的事:爱,就是在绝望里依然紧握的手,是在医生都放弃时,仍然不肯放下的期待。
(王朋宾)
编辑:王嘉琪
责编:肖文翔
审核:吴雪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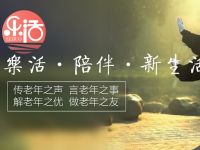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