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 |(桃红岭采风行)那山·那人·那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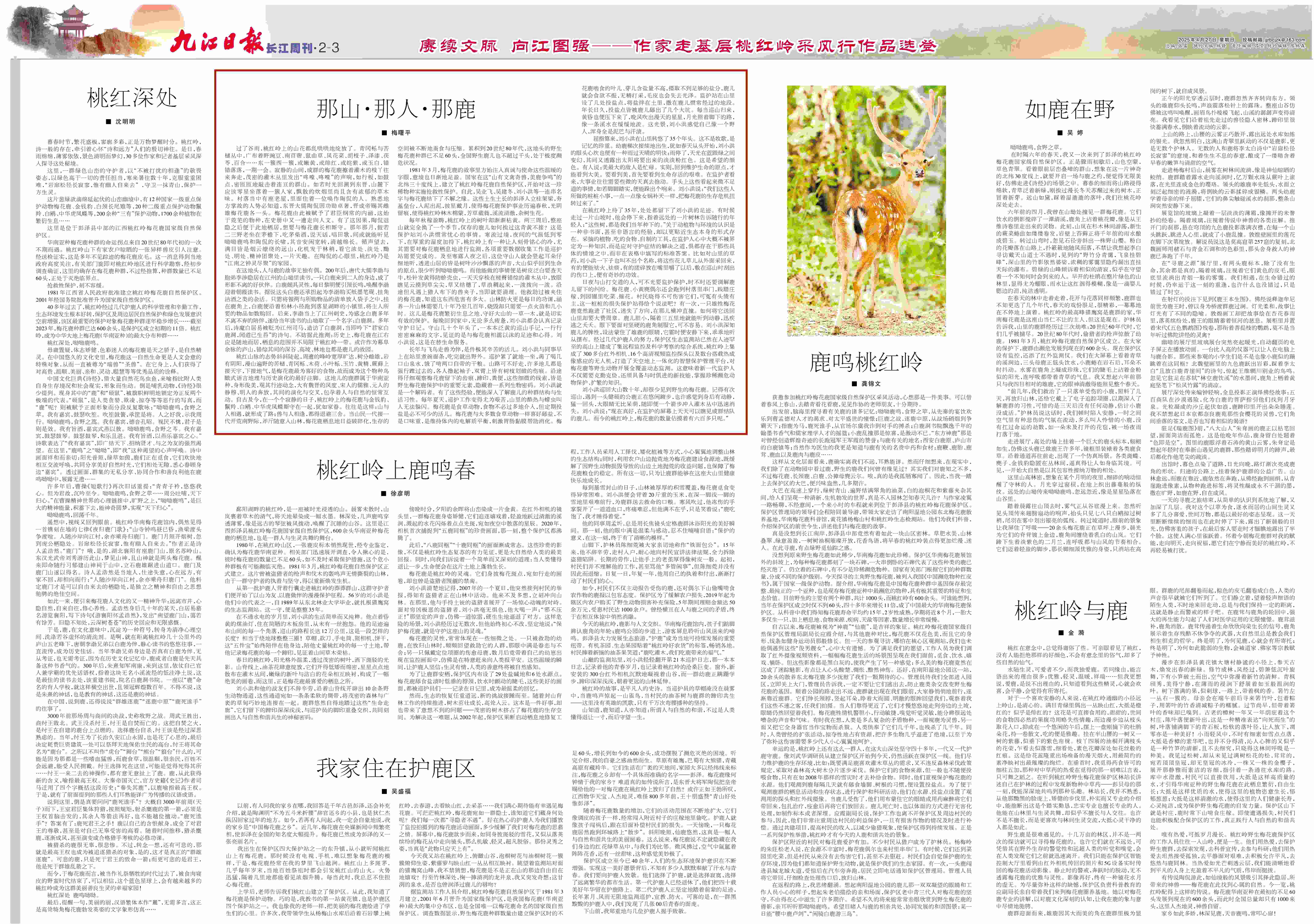
那山·那人·那鹿
■ 梅曙平
过了谷雨,桃红岭上的山花都乱哄哄地绽放了。青冈栎与苦槠丛中,广布着野豌豆、南苜蓿、鼠曲草、风花菜、胡枝子、泽漆、茯苓、百合……东一簇西一簇,或嫩黄,或绯红,或姹紫,或玉白,错错落落,一期一会。寂静的山间,成群的梅花鹿擦着灌木的枝丫往来奔走,茂密的灌木丛里发出“咚嘡、咚嘡”的声响,如行板,如鼓点,密匝匝地敲击着连亘的群山。如若时光回溯到东晋,山麓下应该零星坐落着一簇人家,飘散的炊烟里尚且含有浓郁的草木味。村落当中有座老屋,里面住着一位唤作陶侃的人。熟悉地方掌故的人势必知道,东晋大儒陶侃因功勋卓著,晋成帝赐其雌雄梅花鹿各一头。梅花鹿由此被赋予了君臣纲常的内涵,这始于荒芜的物种,在史册中又一遭走向人文。有了这因果,陶侃退隐之后便于此地栖居,想要与梅花鹿长相厮守。那年那月,假若二三野老坐在茅檐下,吃茅柴酒,说天话,唱田歌,间或就能听见呦呦鹿鸣和陶侃的长啸,其音安闲宽转,清越绵长。循声望去,满目皆是烟云缭绕的远山,化机发于林稍,看它浓处、淡处、黝处、明处、精神团聚处,一片天趣。在陶侃的心眼里,桃红岭乃是“江南之钟灵尽聚”的家园。
在这地头,人与鹿的故事无独有偶。200年后,唐代大儒李渤与胞弟李涉隐居在江州的山坳里读书,一只白鹿来到二人的身边,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白鹿颇具灵性,每日黎明便引颈长鸣,唤醒李渤迎着朝霞读书。据说这头白鹿还承担起为李渤购买纸墨笔砚、挂角沽酒之类的杂活。只需将银两与所购物品的清单放入袋子之中,挂在鹿角上,白鹿便沿着松林小径跑到落星湖畔的小镇里,将主人所要的物品如数购回。后来,李渤当上了江州刺史,为感念白鹿多年不离不弃的陪伴,遂给当年读书的山坳取了一个名字:白鹿洞。多年后,诗魔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造访了白鹿洞,当即吟下“君家白鹿洞,闻道已生苔”的诗句。不妨据此推测:历史上,梅花鹿在江右应是随地而居,栖息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桃红岭一带。或许作为幕阜余脉的庐山,错综其间的深谷、高坡、林地也都是鹿儿的故园。
桃红山脉的态势斜斜陡起,周遭的峰岭宽厚旷达,树分雌雄,岩有阴阳,漫山遍野的苦槠、青冈栎、木荷、小叶栎、玉竹、黄精、蕨藓上接天宇,下接地气,是梅花鹿最为喜好的食物,故而成为这个物种鸟瞰式语言地理与历史演化的最好注脚。这地儿的鹿群属于华南亚种,身形俊美,观其行迹动念,大有魏晋的风度、宋人的儒雅、元人的静穆、明人的奔放,其间的演化与交叉,包孕着人与自然的恒常互动。自古及今,在一个个寂静的日子,桃红岭上的梅花鹿与金钱豹、鬣羚、白鹇、中华虎凤蝶厮守在一起,犹如家眷。往往是这样:山与人相遇,就形成了路;兽与人相逢,都得退避三舍。当山民一代接一代开荒南野际,斧斤随意入山林,梅花鹿栖息地日益破碎化,生存的空间被不断地蚕食与压缩。累积到20世纪80年代,这地头的野生梅花鹿种群已不足60头,全国野生鹿儿也不超过千头,处于极度濒危状况。
1981年3月,梅花鹿的故事里方始注入真诚与使命这些温暖的字眼,意境也日渐地足盈。国家在这“山有文禽奇兽,美鹿争鸣”的北纬三十度线上,建立了桃红岭梅花鹿自然保护区,开始对这一珍稀物种实施抢救性保护。自此,吴业飞、吴建冬、刘小洪等一连串名字与梅花鹿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土生土长的彭泽人立柱架梁,夯基垒台,入泥出泥,披星戴月,使得梅花鹿保护事业历遍春秋,光阴留痕,使得桃红岭林木棉蒙,芳草葳蕤,溪流清澈,杂树生花。
每年秋稼盈畴,桃红岭上的树叶却渐渐枯黄。两三周后,整座山就完全换了一个季节,仅存的鹿儿如何挨过这青黄不接?这是保护站刘小洪惯常忧心的事情。寒流过境,夜间的气温低到零下,在厚重的湿度加持下,桃红岭上有一种让人刻骨铭心的冷,尤其需要对梅花鹿栖息地进行监测,各项重要数据收集工作是巡护站需要完成的。及至寒露入夜之后,这位守山人就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透进山居的皆是树叶沙沙飘落的声音,大山似乎回到生命的原点,很少听到呦呦鹿鸣。而他能做的事情便是树皮泛白要查天牛,松针发黄得防蚧壳虫,一天天穿梭在槎枒错综的灌木丛中,放眼瞧见云摸到草尖尖,草又结穗了,草浪稠起来,一泼拨向一泼。沿途但凡遇上猎人布下的兽夹子,当即就要清理。他救助过被夹住的梅花鹿,知道这东西危害有多大。山林防火更是每日的功课,涵养一片山林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烧毁却只需要一点火苗和几小时。这儿是梅花鹿繁衍生息之地,守好大山的一草一木,就是切实有效的保护。每晚回到家中,无论多么疲惫,刘小洪都会认真记录守护日记。守山几十个年头了,一本本泛黄的巡山手记,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文字,见证的是与梅花鹿相濡以沫的足迹和心得。刘小洪说,这是在替生命服务。
长年与飞鸟走兽为伴,是件极其辛苦的活儿。刘小洪与同事早上在站里煮碗面条,吃完就出野外。巡护累了就地一坐,渴了喝几口山泉水,饿了啃两口自带的干粮。山路可不好走,许多地儿都是强行蹚过去的,各人撸起袖子,双臂上皆有树枝划破的伤痕。沿途得仔细观察梅花鹿留下的齿痕、蹄印、粪便,这些细微的线索,皆是野生梅花鹿保护中的重要元素,隐藏着一系列生物密码。刘小洪就是一个解码者。有了这些经验,便能深入了解鹿儿的种群结构与生活习性。每年夏天,巡护工作变得尤为艰苦,山里的酷热与蠓虫叫人无法躲闪。梅花鹿是食草动物,食物不必过多地介入,但定期投盐是必不可少的活儿。梅花鹿与大多数食草动物一样喜好舔盐,不是口味重,是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刺激胃肠黏膜帮助消化。梅花鹿啮食的叶儿、芽儿含盐量不高,摄取不到足够的盐分,鹿儿就会食欲不振,无精打采,毛皮也会失去光泽。监护站在山里设了几处投盐点,将盐拌在土里,撒在鹿儿惯常经过的地段。年长日久,投盐点皆被鹿儿舔出了几个大坑。每当巡山归来,黄昏也便压下来了,晚风吹出漫天的星星,月光照着脚下的路,像一条溪水在缓缓地流。这光景,刘小洪感觉自己像一个野人,浑身全是泥巴与汗渍。
屈指算来,刘小洪在山里转悠了35个年头。这不是牧歌,是记忆的珍重。幼鹿梯次接续地出生,犹如春天从头开始,刘小洪的眼头心坎也便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明快:雨停了,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粉红色。这是希望的颜色。有人说:美最大的敌人是忙碌。实则,回到维护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大美。要看到美,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在监护者看来,大事业往往需要些微的天真去推动。手头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如若脚脚踏实,便能跺出个响来。刘小洪说:“我们这些人所做的桩桩小事,一点一点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梅花鹿的生存危机扭转过来了。”
在桃红岭上待了35年,处处都留下了刘小洪的足迹。有时候走过一片山坡时,他会停下来,指着远处的一片树林告诉随行的年轻人:“这些树,都是我们当年种下的。”关于动植物与环境的认识是一种非书面,甚至非语言的经验,却以更贴近生态本身的形式存在。采摘的植物、吃的食物、自制的工具,在监护人心中大概不被界定为一种知识,而是应对守护症结的解决之道,俱都存在于那些具体的情境之中,而非在表格中填写的标准答案。比如对山里的草药,刘小洪一下子也叫不出个名称,将这些花儿草儿从外面采回来,有的便能祛火、祛痰,有的搓碎放在嘴里嚼了以后,敷在巡山时刮出的伤口上,便有奇妙的功效。
日夜与山打交道的人,可不光要监护保护,时不时还要调解鹿儿留下的纠纷。梅花鹿、小黄麂偶尔还会跑到村落里串门,践踏庄稼、到园圃里吃菜、摧花。村民晓得不可伤害它们,可冤有头债有主,这一桩桩的损失保护站得给个说法吧?有一次,一只雄性梅花鹿竟然跑进了社区,迷失了方向,在那儿横冲直撞。如何将它送回山里却要大费周章。鹿儿胆小,隔着三五里地就能听到动静,迅疾逃之夭夭。眼下要面对坚硬的鹿角制服它,可不容易。刘小洪深知鹿儿的脾性,设法蒙住了雄鹿的眼睛,它霎时便安静下来,乖乖地听从摆布。经过几代护鹿人的努力,保护区生态监测站已然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上建成了集远程监控及科学考察的综合系统,桃红岭上集成了300多台红外相机、16个高清视频监控探头以及数台搭载热成像感应的无人机,打造了天空地上一体化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对梅花鹿等野生动物开展全覆盖动态监测。这意味着新一代监护人不仅需要克勤克俭,还须具备与时俱进的新技能,掌握珍稀濒危动物保护、扩繁的知识。
刘小洪巡回大山数十年,却很少见到野生的梅花鹿。记得有次巡山,遇到一头健硕的公鹿正在悠闲踱步,也许感觉到身后有动静,猛一回头,大眼睛无比呆萌,随即便一个箭步冲入灌木丛中迅速消失。刘小洪说:“现在真好,在监护的屏幕上天天可以瞧见成群结队的鹿儿。而今的桃红岭上,梅花鹿的数量估摸着有六百多只呢。”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吴晨
责编:肖文翔
审核:朱静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