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 | (讲述)我与杨国凡老师的交往

■ 陈林森
杨国凡原名国藩,自号闲斋。杨老师是星子县(今庐山市)的文坛耆宿,原星子中学的语文泰斗,也是我的良师益友。自从相识、共事直到先生生命的尽头,我与杨老师的交往前后持续了30余年。
1982年我从农村中学调到县中,初见杨老师,他就慈眉善目、满脸笑容地紧握我的双手,连称“神交”。我受宠若惊,心想这个词应当从我口里说出来才好。我早就听说杨老师与余福智老师是20世纪60年代时,星子教坛颇负盛名的两位语文大师,也听过杨老师的学生对他教学水平的赞扬。初来乍到,举目无亲,杨老师和我第一次见面之际,就热情邀请我当晚去他家做客,为我接风。当时他是语文教研组长,后来被提为教务副主任。他亲自领导创办文学社,和我们青年教师一起组织、指导学生开展语文课外活动。文学社和油印刊物的名称就是他命名的,叫作“荷角”,寄托了他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我初到县中,专注教学,他随堂听课,切磋教艺,帮助我消解教学的难点。除了指导我的业务,他还鼓励我业余创作。我偶有新诗涂鸦,便向杨老师求教,他都热情肯定,并推荐到县文联办的小报上发表。1986年,他推举我接任语文教研组长。他对我的器重和垂爱,甚至达到了“逢人说项”的地步。尽管由于我的努力不够,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但至今回想,对他的知遇之恩依然十分感动。
我刚到县中,只有30多岁,还踩着青年的尾巴。杨老师也不到50岁,尚属壮龄。我在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是能够做些事的,可惜我俩共事的时间只有四个春秋。“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他离开县中以后,我一直与他保持联系。1986年,为了子女,他提前退休。翌年,湖南师大老教授、岳麓诗社社长高扬诚邀他赴湘担任《岳麓诗词》杂志常务编委。这是他在特殊年代关进牛棚之后,又一次离家独居。我开始与杨老师书信联系。他在来信中流露了思家之情,字里行间也有“举目无亲”之慨。我便给在长沙的四姐写信,请她在方便的时候对杨老师予以关照。后来杨老师应邀到我四姐家做客,还和年龄相仿的姐夫相谈甚欢,成为朋友。告别湖南的编辑岗位后,杨老师又受邀到云南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可惜他不适应边境地区的水土,提前返乡。后来杨老师再也没有外出,除参与五柳诗社等本地文化活动以外,一直在家著书立说,致力于诗词研究和诗词创作以及古代先贤陶渊明的研究。2013年以后,杨老师身体欠佳,很少出门。我偶尔在街上遇见杨老师蹒跚的身影时,他即使拄着拐杖,依然笑容满面,对我嘘寒问暖。在那期间,我多次登门拜瞻,亲聆謦欬。
2014年2月10日是正月十一,当天下午,我又一次去杨府造访。从南门到蔡家岭步行大约半个小时,出门后下起了小雪。我到的时候,杨老师刚从床上坐起。因为天气比较冷,我劝他不要起身,便在卧榻前与他聊天。师母端茶敬烟,开了取暖器,杨老师吩咐她拿本书送我。
几乎每次到杨家拜访,我都能获赠一本书。之前最多的是《闲斋诗话》,一本又一本地出。上一次送我的是《诗经新译》,厚厚的一大本。这次惠赠的是《闲斋絮语》,是随笔性质的文集。杨老师说,年前1984届学生举行毕业30周年聚会,他把这本书赶印出来,参加聚会的师生每人一本。
杨老师说他已八十初度了,这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买书、教书、写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说某人“笔耕不辍”,多半是夸张,可杨老师是身体力行。几十年来,他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词、曲、联2000余首(副),诗话、诗评、史评以及教研文章、陶研论文近百万字,有多部专著和诗集出版。在星子文化界,他众望所归,创办“五柳诗社”,为首任社长。他淡泊名利,不屑钻营,专事著述,乐此不疲。他为书房题名为“闲斋”,既有“闲情逸致”的含意,又有“闲云野鹤”的志趣。他在一首《陇头泉·退休自嘲》的词中写道:“望南山,闲云出岫;辞马帐,倦鸟归林。达既无能,遑论兼济,便该穷处善吾身。聊自慰,闲斋晚辟,笔砚乐耕耘。”他为人随和,诲人不倦,每有登门,有教无类,指导不同水平的社员练习诗词,不少弟子尔后成为当地诗坛的中坚。我到他家,有时他会拿出一首作者的原稿给我看,一边指点,一边批评得失,告诉我应当如何修改,怎么合律,我从中受益匪浅,感佩良多。杨老师诗歌的稿纸,总是高高地堆放在宽大的书案上。
杨老师半倚着床榻说,2013年他出书用掉了几万元。他退休工资三千多,积蓄也不会很多。他说儿女若有急难,他可以资助点,但不准备把钱全部留给儿孙。这些书,儿女们要就拿去,不感兴趣就算了。我想杨老师的子女不反对他这样做,就是对他的支持。我问杨老师,出这些书,有没有得到过一些赞助?他说,都是自费。如果从功利的眼光来看,杨老师的劳动几乎是没有回报的;如果说对社会的影响,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也会受到相当的制约。可社会上总有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市场经济的投入产出规律背道而驰,也与物质层面的欲求背道而驰,甚至与子女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在文化领域开辟一块小小的园地,终其一生,或者终其退休生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用一本又一本聊以自慰却很难卖出去的书,围成自己生命的年轮。
2015年11月14日,杨国凡老师因病离世,享年81岁。他的学生、同事、诗友、忘年交,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先生洒下不舍的热泪。杨老师留下遗嘱,他的墓志铭命我忝为执笔。在铭文中,我这样概括杨老师退休以后在地方文化方面的功德:“公晚年潜心学问,长诗社,著诗话,研陶学,注六经。惜乎百载难期,赍志未竟,此君子所尤痛心也。”在人们的心目中,杨老师似乎是一位“老派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保守。在研究和探讨中,他吸纳现代思维,与时俱进。
今年是杨国凡老师辞世十周年。我谨用这篇小文,对杨公的学识与风度遥致敬意。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嘉琪
责编:肖文翔
审核:熊焕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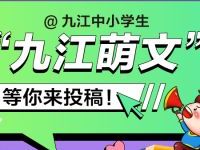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