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九江丨云雾深处栖贤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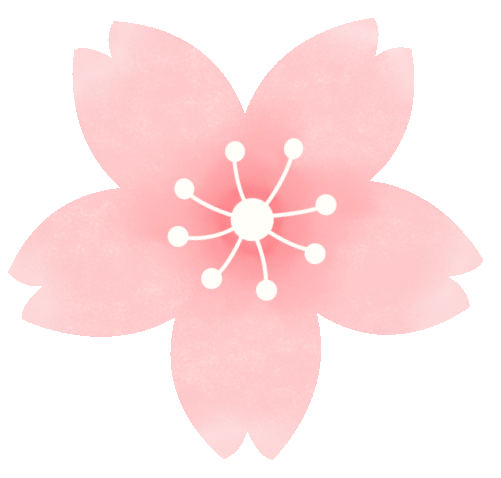
□ 沈明明
浔阳城内有座思贤桥,庐山深处有座栖贤寺。思贤桥上好钓鱼,栖贤寺外好看云。钓鱼也好,看云也好,总会想起唐朝那位贤人来。江州浔阳大概是他的最爱,更不用说处处幽静的庐山了。他叫李渤。他做过官,是位清廉的官;他爱读书,读出了中国书院寺庙文化。
李渤,在庐山五老峰下与白鹿相伴读书,读出了举世无双的白鹿洞书院;在庐山石人峰下读书,读出了五大丛林之一栖贤寺。那些年,他读着书,精神徘徊在方内方外,身边的书读完了,求知欲不但没有满足,反而更强烈了。他决定去拜访一位高人。那位高人就在庐山金轮峰下归宗寺。那寺原本是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私建的别墅。王羲之走了,和尚来了。几百年过去了,来了智超禅师。羲之别墅,在他手里,洗心革面,来了次超然脱俗的华丽转身,成了禅宗修行庄严庙宇。香烟袅袅,飘上了金轮峰。
李渤想到的高人就是智超。
李渤的处世贤德,方外的智超也是晓得的。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缘,互以欣赏目光打量对方,惺惺相惜。金轮峰转到了石人峰,李渤的书斋,也来次转身,成了庄严庙宇。智超思量再三,做出了最后决定,将庙宇命名为栖贤。李渤的读书栖身处,便是栖贤。而在李渤的心中,智超是真正杰出的“灵魂工作者”,感言称赞智超:“出廓送钱嫌不要,手提棕笠向庐山。昔日曾闻青霄鹤,更有青霄鹤不如。”
一僧一官,相互倾慕,互为知己,传出了佳话。
自此往后,文人名士,不惧旅途艰辛,爬山涉水,照样纷至沓来。“贤人”和“闲人”越来越多,栖贤寺,越来越名副其实了。
欧阳修不只是来了,还欣然捉笔,题诗山僧:“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五百僧”?便是欧阳修无意中的这几个字,几百年后引出了一段让栖贤寺身价爆表且命运多舛的故事。此处暂时按下不表,容后道来。
那天,朱熹来了,他是来履新南康(今九江及庐山市一带)知军的。一路上很兴奋,尤其是听到栖贤寺及陶渊明李渤等人的故事,一向庄严肃穆的他,也不守规矩地“戏作”起来:“长官定笑归来晚,中允应嫌去却回。惟有山人莫相笑,也曾还俗做官来。”对于乌纱官帽,渊明李渤们是不看重的,朱熹却是十分在意,这是他们的不同。然而,酷爱读书为学酷爱教书育人,则是他们的相同。这不,就在不远处,这个李渤当作书斋的白鹿洞,被南康知军朱熹改造成了宋朝版的最高学府。
宋高宗钦点的进士第一(状元),王十朋,也来了,来了便有些不想走,于是自己挽留自己,住了多日,夜晚多梦,似醒似睡:“瀑水声中夜不眠,星河影动半秋天。谁云滟滪瞿塘远,只在扬澜左蠡边。狮子吼成方外法。石人参得定中禅。住山五老知今古,借问曾栖几个贤?”亲身体验,才知道什么是高山仰止,一种崇高感油然而生,于是,王十朋想问五老峰,在这里住过的,能不能都算是贤人,我也来了住了,算得一个“贤”么?短暂的栖贤寺“镀金”之旅,让王十朋感到心境走进了一个崭新世界。
苏轼号称居士,却无心于“方外法”“定中禅”,视线牢牢被栖贤寺旁三峡水石所吸引:“吾闻泰山石,积日穿线溜。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深行九地底,险出三峡右。长输不尽溪,欲满无底窦。跳波翻潜鱼,震响落飞狖。清寒入山谷,草木尽坚瘦。空濛烟雨间,澒洞金石奏。弯弯飞桥出,潋潋半月彀。玉渊神龙近,雨雹乱晴昼。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今天,来栖贤寺橹断泉处等候取水饮用的居民游客,需要排着长队,孰知苏轼早就排在他们前头老远呢?“可咽不可漱”,足见此处甘冽山泉是何等的琼浆玉液!
这是飞流、乱石、古木、峰峦、云雾、寺院奢华组合的全景。沁入心肺的,更有清新无双绝无杂染的气息。中国古人虽然知道生命在于呼吸,却并不知道生命呼吸的是“空气”,否则,他们的生辉妙笔,该将这里的空气描成啥样的蓬莱仙味?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栖贤寺等来了一位结缘人金世扬(号铁山,今辽宁“大城市”铁岭人)。是年,他游学匡庐,为灵山圣水所震撼。许下誓言,来年发迹后,一定买田匡麓以膳山僧。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金世扬果然“发迹”迁升苏洲布政使,主管全省财政人事。他不忘初心,或是受了欧阳修那“五百僧”的点拨启发,以千金重酬礼请浙江画家许从龙创作罗汉图。整个艺术创作历时六、七年,终大功告成。康熙壬辰年(公元1712年)四月初七,金世扬将装璜精妙的两百幅《五百罗汉图》经水运直送栖贤寺。据载:图“幅广五尺,长一丈四尺有奇,法像大者高三四尺,小者可尺许,或援笔立成,或旬日乃写一像,毛发纤悉皆具,行坐笑语,杂出于山海、木石、鱼龙、鸟兽之间。变化无方,而端严清净之心穆乎可想。”“每幅两三人,或三四人,趺坐者、肩行者、虬髯突睛者、低眉入定者、踏螺蟹涉波涛者、乘云雾履山涧者,身披衲衣,耳缀大环,或赤足,或草履,或头陀戴金刚圈。山林之岑寂,海涛之汩没,花树木石之奇诡,鱼龙鸟兽之变幻,殊形异状,难以缕述。”画中罗汉们,栩栩如生,变化万千。
康有为在栖贤寺见此图后,惊叹一声:“庐阜镇山之宝”!
既是宝物,自然招来觊觎。1854年,太平军焚烧栖贤寺等,两百幅罗汉图随寺被毁78幅。民国初,两位洋人借口游玩,趁寺庙和尚烧水沏茶时,盗走2幅,不久又被军阀强购1幅。1939年和1940年星子伪县长罗福初两次强行索取7幅赠送日寇献媚。
解放后,1幅存于南京博物馆,其余112幅被送庐山博物馆保存。
历史的天空,总在翻动变幻着风云,就像眼前栖贤寺的上空。
“名重於诸刹,前贤旧隐踪。无人知有路,隔树忽闻钟。瀑壮山疑裂,云深树若封。或传遗稿在,三叩昔时松。”宋时毛珝的这首《庐山栖贤寺》,有些暗合我时下的心境。诗中所言“隐踪”“隔树”“云深”“无人”等等,让人心生云雾,视线迷离,在这大山深谷远离尘世的静谧时空里,只听得山泉哗哗流过……若是用心寻觅,只要来次全景转身,便越过了鸿沟,听得见光明彼岸的深情呼唤。
栖贤寺,或许可以易名“栖闲寺”。因为,只要跨过那座三峡桥,一定能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闲情逸致,不空寂落寞,是充实丰盈!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嘉琪
责编:钟千惠
审核:熊焕唐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