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岁月丨老歌之恋
或许天性使然,我打小就酷爱唱歌,虽说如今已古稀之年,但这种以词与曲制作的精美艺术,仍活跃于我那日渐衰弱的大脑皮层和大不如前的歌喉,尤其是那些已被淡忘却叫人刻骨铭心的老歌!
若说时间最长的老歌,当数幼时在家学唱的儿歌。这些通身都弥漫着乡土气息的歌专属幼童们吟唱,至于它产于何年何月,授我歌者奶奶也只说她亦是她奶奶所传。这些儿歌旋律简单易学,歌词朗朗上口。譬如《鸟儿叫》,词曰“鸟儿叫,尾巴拖,三岁宝宝会唱歌。不是爹娘教给我,是我聪明学来的歌”;又如《打掌掌》,词曰“打掌掌,百花开,风吹杨柳过江来。船在江里走,花在岸上开”。显然,前者鼓励幼童从小就要树立自信心;后者则用几处春景之“元素”,引导孩子感知春天的气息。可惜我那时无法参悟这些丰富意境,只是一边很乐意地一字一句强记,一边偎在奶奶柔软的怀抱里,尽情享受老人家眼眸里洒落的那一抹爱怜。
直到1963年我背着书包走进课堂,我才真正与那些由专家们作词作曲的歌邂逅并结缘,随着个人思维和认知能力的提升,我也逐渐悟出唱歌的深邃意义,一个以潜移默化为通道,给人思想和精神提供丰富养分的平台。故而,像学习语文、数学等主要课程一样,我全身心投入每一堂音乐课,心神专注地跟老师学乐理知识,学唱歌技巧;但凡遇上自己钟爱的歌曲,一定会格外用心记、用心唱,像《一分钱》《让我们荡起双桨》《花儿朵朵向太阳》《小松树》《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北京的金山上》等数十首歌曲,我皆能烂熟于心,随口而就。这里还颇值一提,这些歌曲我们并不是关在教室里自娱自乐,而是经常把它们带出校外,馈赠给田畈地垄,青山绿水!譬如清明节去烈士墓地扫墓,或队日赴孤寡老人家“做好事”,我们都穿戴整洁,佩戴红领巾,在迎风猎猎的队旗引领下,一边昂首阔步前行,一边用清脆悦耳的童声,把《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唱得高亢嘹亮,激情飞扬,以至田间地头、道旁路边的人都忍不住放下手中活计向我们点头致意……
而当1973年我从共大毕业返乡后,职业身份由“生产队社员”到“大队团支书”再到“中学老师”;在这数十年的时空里,特别是青壮年时期,我爱唱歌的秉性依旧一如既往,只是遗憾那时的乡村文娱资源十分匮乏,别说录音机,就连收音机也没几家有,更莫谈电视机,获得歌曲的途径少之又少。故此,一旦好不容易在公社有线广播中或在一个月难得遇上一次的露天电影里,发现有自己喜爱的歌曲,别无选择,只得以强记的方式,反反复复练唱。那年,一位好友捎信给我,说他弄到一本很时兴的《革命歌曲选集》,集内收录了诸如《长征组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一系列时尚歌曲。我喜出望外,迫不及待跑了几里路去他家借阅。之后二十多天利用早起晚睡时间,硬生生将其中80%的歌曲一笔一画誊抄下来,并让母亲将其一针一线装订成册……
简单归纳一下,那阵子被我挚爱并熟记的歌曲大抵有四类。其一,儿歌。它们是第一拨最先走进我的生活,也是最先被我珍藏于胸的歌。在我的印象里,这些儿歌就像是一堆五颜六色、香甜可口的棒棒糖,时常掏出来“闻一闻”或“尝一尝”,很容易让自己想起那一段天真烂漫、甜香四溢的童年生活……其二,民歌。它们都是在民间流传甚久的古歌,皆因旋律优美、意境深远之特点,被后世以口口相传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在我的感知里,它们就是一件件表面无影无形却满身岁月印痕的古文物。一唱起来,思维的触角往往会穿越时空,伸向那个久远的年代,去探寻和感受先辈们的生活境况……其三,红歌。这些歌拥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社会发展前行的“风向标”。它所蕴含的爱国、富强、坚毅、公正、友善等这些闪烁正能量光辉的理念,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憧憬、追求、向往同频共振……其四,电影插曲。原本也属“红歌”范畴,之所以把它剥离独立,是因为它既是我们获取歌曲的最主要途径,亦是人气最高、宠爱最甚、精品最多的好歌之产地;更关键是,我们获取它的方式,不是单纯地从广播里“听”或在歌集中“看”,而是通过其“歌声”与“画面”交相照应而形成的立体效果,辅之我们感知、提升、巩固对歌曲的直观记忆,以加快习歌进程……
如同人的一日三顿不可缺,我把唱歌视为生活中的必需,到了痴迷程度。那年母亲就当面对我抱怨一通:“你呀你,走也唱,坐也唱,躺也唱,连吃饭嘴里也不消停!到了半夜还趴在桌上写呀、哼呀!孩子,唱歌就这么重要么?”我一位堂哥也曾在我家指着桌上几本我手抄的歌集,半开玩笑半嘲谑对我说:“费时费力,劳神劳心!兄弟呀,这是何苦来?”我当时虽不置可否一笑回应,心里却在对他说:哥,你咋就不能善解人意呢?俗语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既爱之,自有爱的道理呗!倘现在你我交换位置,相信歌喉一开,你的心也会随之被温暖、被愉悦、被澎湃……
一年一度的“开秧门”(春插第一天)如期而至。为讨个好彩头,凌晨四点,生产队长就敲响开工的钟声。大家纷纷踩着星光拥向母秧田,各自施展最好的拔秧技术,让身后不久便排起一列长长秧把队伍。此时,八旬梅婆给我们送茶烟来了。那茶,是香喷喷桂花茶;那烟,是价钱不菲的“大前门”。按老规矩,我立马亮开嗓门敬献送茶人一曲《插秧歌》:“嗬嗬哟嗬哟嗬,一年四季吔在于春啰,打个秧歌开秧门哟。多谢梅婆请香茶啰,来日五谷吔齐丰登哟……”伴着歌声,东方渐露曙色;不久,太阳出来了,天地间一片红光……
“双抢”进入最紧张时段。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我也是其中一员)一字儿排开,挥镰割一片又一片金黄稻子。由于连续几天争分夺秒,加之烈日炙烤难耐,割稻的速度明显减慢了。这当儿,民兵小队长淼哥突然引颈高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旋即,大家齐声跟唱起来“……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水深,高举革命的大旗,巨浪滚滚永不停……”高亢的歌声中,银镰飞舞,新一波你追我赶的热潮开始了……
吃罢晚饭,我们文艺宣传队18人打着手电,迎着山风,穿过1.5公里狭长山垅,准时赶到陈凹人为我们演出准备的“戏台”。先是大合唱,再是舞蹈;接着又是女声小合唱……一时间,悦耳悠扬的歌声恣意在夜空飘荡,混杂着观众们的欢声笑语,填满了这个被四面峰峦怀抱、人们戏称“自治区”的山旮旯……
“踏青”时节,我领着全班同学登至附近最高山峰观赏春色。举目远眺,连绵不绝的山峰,蜿蜒清亮的小河,柔曼轻盈的白云,鳞次栉比的山地,嫩绿肥沃的田畴,苍劲挺拔的松林……触景生情,我禁不住脱口唱起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同学们先是惊奇,继而围上来要求教他们唱。我没拒绝,一边讲解这首歌的出处和意义,一边逐字逐句教他们唱:“一层层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同学们都唱得很认真,也很动情。许多年后,有学生还跟我说他仍然记得我给他们上了一堂以热爱家乡为主题的特殊音乐课。
“五四”青年节集会在公社广场举行,各大队、各机关单位青年已列队入场就位。按惯例,会前各单位之间“赛歌”(也称“拉歌”)活动拉开了帷幕。但见蓝天白云下,数千人聚于一场,数百人一齐高唱。人人竭尽全力,个个不甘落后。此时此刻即便不擅唱歌的人,也忍不住张开嘴跟着和起来,且不管是唱好唱差,喉咙是痛是哑,结果是输是赢,因为尽心尽力唱了,谁的脸都是灿灿的,心都是美美的……
时过境迁,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这些被千千万万人交口传唱的绝大部分歌曲悄然告别历史舞台,被人们冠以“老歌”深藏于心底。只是我怀旧情结浓厚,尽管“中气”业已不足,“音准”已然有失,还是忍不住经常从心底掏出来唱一唱,借以怀念一番那一段激情四射的岁月。
(郤正钦)
编辑:方旬瑜
责编:肖文翔
审核:朱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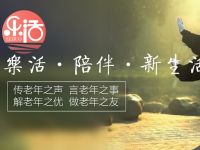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