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 | (论语)独特视角下的绝世美景——也说张岱的《湖心亭看雪》

独特视角下的绝世美景
——也说张岱的《湖心亭看雪》
■ 邱益莲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而境又分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张岱写湖心亭上看雪,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浑然一体,营造了一幅世间绝美的图画。
按常理,看雪自然应该是从视觉写起。岑参在大雪纷飞的时候送别朋友,想到朋友终于得到升迁的机会,能从边地返回京城,既为朋友开心,也充满着艳羡,更是对自己离开这奇寒之地的一种美好期盼。因为有着盛唐文人的自信,他坚信下一个就轮到自己回京升迁,于是,他的视觉里的雪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飞雪之后就是姹紫嫣红的春天。可张岱却随性挥洒,越过常规,偏从听觉着笔:“湖中人鸟声俱绝”。“人鸟声俱绝”,是指人与鸟的声音全绝迹了。为何绝迹?作者是从侧面来回应“大雪三日”的雪之大,大到鸟不敢飞,人不敢走,营造了一个千里冰封、万籁俱寂的空旷苍茫无我之境。用听觉来侧面写雪后满世界的空寂辽阔,这手法当然不是张岱首创,唐人柳宗元独立雪后寒江,他就通过写视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来侧面烘托雪大,营造了一种凄寒无边的境界,让人感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同样是白茫茫的世界,张岱因当时为富贵公子,他看雪是为了寻找山水之乐,这种空旷给他的是内心的宁静。而柳宗元笔下的空茫,恰恰是他改革失败后看不到出口的一种绝望。
更定时分出发,有说更定是天将晓,也有说是刚入夜,作者选择这么一个避开人流的时间去看雪,驾一叶扁舟漂浮在白雪茫茫的大湖之上,只见湖中的雾气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冰花,“天”“云”“山”“水”上下一体,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白茫茫的、浑然一体的世界。因为有了世界的阔大,自然就有舟的渺小,人的渺小,物的渺小。置身在无边无际、天地一体的白茫茫之境,远处的长堤隐约只是白色画面上一道灰黑的痕迹,湖心亭只是一个小点,湖上小舟像一片草芥,舟中的人更是微小到一粒一粒,就像粟米。湖上长影,远处湖堤,湖心亭子,张岱是可以从船上观察得到的。但是,作者身在舟中,无法识其真面目。于是,作者采取分身法,充分发挥想象力,从远处对小舟和人在大雪覆盖的湖面的形象进行全方位臆测,想象出沧海与一粟的反差效果。张岱就像一位丹青妙手,在空蒙的背景上,几笔勾勒出一幅浓淡相宜、远近搭配、动静结合的山水图画,给人一种纤尘不染、与世隔绝的纯净素雅之美。这样的美景,让人望峰息心,窥谷忘反。
如果说,湖上看雪是一绝,那么登上亭子,遇到的人事,又是一大奇,作者自自然然由无我之境转为有我之境。“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几句简单的勾画,便给人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两人铺毡对坐,想必是意趣相投的朋友在促膝而谈。一童子在煮酒,酒正烧滚沸腾。人物的静,与酒炉的动,构成一幅安详怡然的画面。而这画面又镶嵌在亭子里,整个亭子又镶嵌在白雪皑皑的湖心世界,这种景与人相映成趣的宁静画面,不正是作者追求的安闲之趣吗?
《核舟记》里有个画面,“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这是记明奇巧人王叔远在径寸核桃上雕刻苏东坡、黄庭坚、佛印三位好朋友的生活情状的事,但整个画面却是以明代文人的生活雅趣为参照的。在表达方式与画面质感上,《核舟记》里这幅画面与上文写亭中人物的画面是高度契合的,都是以一望无际的江湖水面为背景,足见明代文人雅士的情趣是很有相通之处的。
避开人声鼎沸的时段登亭,本为图个清静,哪知湖上更有早行人。此时,作者应该有感触,有表情,深感意外。可是作者却不写自己的感受,用飞来之笔,从对方入手,反客为主,用“见余,大喜”四字来写对方的反应,在冷静中平添波澜。
大雪三天,人鸟绝迹,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的时候独往湖心亭看雪,一个“独”字,写尽作者独抱冰雪之操和孤高自赏的隐幽之趣,更是透出“噫,微斯人,吾谁与归”的人生孤独。可是,登上湖心亭,那里早有人在,无意间发现竟有人和自己有不谋而合的想法。偶遇知音的兴奋,又何止是对方,作者其实也是万分欣喜的。可作者偏对自己不着半字,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来看待对方的行色举止。所以,当对方惊呼“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时,其实也是作者内心的惊叹。“拉余同饮”,一个“拉”字,不仅写出了对方的热情,更写出了酒逢知己,惺惺相惜的深情。这场景,很有杜氏“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豪侠之气。
酒逢知己自是千杯嫌少,“强饮三大白”,一个“强”字,不仅写出了作者因意外遇见同道之人的兴奋,超越平时酒量的豪饮,也透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孤傲。常人相遇,一般先问彼此姓名。可作者和湖心亭上两人相遇,不落俗套,见面只是喝酒,大有知己不问出处之势。临别,问取对方姓氏,才知是金陵人氏,客居于此。看似是闲来之笔,却体现了作者笔法的摇曳多姿,并隐藏深意:这二人从金陵客居于此,又哪是寻常之辈?在人鸟声俱绝之际早早登上湖心亭的客人,其实是隐逸于此的高蹈之士。
明代文人高士的雅与俗,痴与慧,在天地漠然的无人之境与有人之境中浑然一体,被作者寥寥几笔就刻画得淋漓尽致,最后以舟子的喃喃自语作结,“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舟子,是深深理解作者的人,他就像《赤壁赋》中那个吹洞箫的客。本文的舟子,恐怕就是作者的另一个角色,在替作者完成世俗的观察。在欣赏完这幅绝美的图画时,不得不惊叹作者布局、构思、运笔之奇妙。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吴晨
责编:肖文翔
审核:杨春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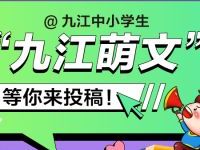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