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九江 | (名家有约)历史骨缝中的光(之一)航海图 钓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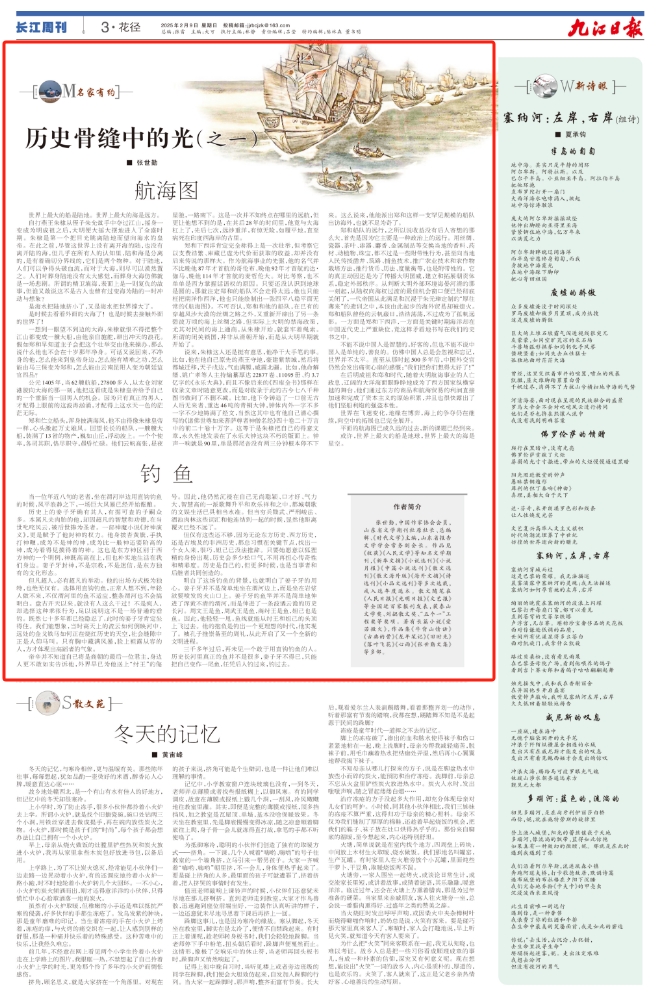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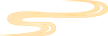
■ 张世勤
航海图
世界上最大的船是陆地。世界上最大的海是远方。
自打燕王朱棣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过江山,摇身一变成为明成祖之后,大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朱棣是第一个把目光眺离陆地而望向海水的皇帝。在此之前,尽管这世界上没有离开海的陆,也没有离开陆的海,但几乎在所有人的认知里,陆和海是分离的,是有着确切分界线的,它们是两个物种。对于陆地,人们可以争得头破血流,而对于大海,则尽可以漠然置之。人们对葬身陆地没有太大感觉,而葬身大海仿佛就是一场悲剧。所谓的精卫填海,表面上是一则复仇的故事,但谁又敢说这不是古人也曾有过变海为陆的一时冲动与想象?
是海水把陆地挤小了,又是海水把世界撑大了。
是时候去看看外面的大海了!也是时候去接触外面的世界了!
一想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朱棣就恨不得把整个江山都变成一艘大船,由他亲自施舵,耕出冲天的浪花。假如郑和早知道主子会把这个壮举交由他来操办,那么说什么他也不会在十岁那年净身。可话又说回来,不净身的他,怎么能来到皇帝身边,怎么能有靖难之功,怎么能由马三保变为郑和,怎么能由云南昆阳人变为朝廷监官四品?
公元1405年,当62艘航船,27800多人,从太仓刘家港驶向大海的那一刻,他把这看成是朱棣皇帝给予自己的一个重新当一回男人的机会。因为只有真正的男人,才配得上眼前的这波涛汹涌,才配得上这水天一色的茫茫无际。
郑和伫立船头,浑身披满海风,他不由得像朱棣皇帝一样,心头激起万丈雄风。回望长长的船队,一艘艘大船,装满了13省的物产,巍如山丘,浮动波上。一个个使卒,各司其职,恪尽职守,晨昏忙碌。他们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一路南下。这是一次并不知终点在哪里的远航,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其后28年的时间里,他竟与大海杠上了,先后七次,远涉重洋,有惊无险,如履平地,直至病死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
郑和下西洋肯定完全称得上是一次壮举,但考察它以支费浩繁、库藏已虚为代价而获取的收益,却并没有后来传说的那样大。作为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名气并不比晚他87年才首航的哥伦布、晚他92年才首航的达·伽马、晚他114年才首航的麦哲伦大。对比考察,也不单单是西方掌握话语权的原因。只要还没认识到地球是圆的,那就注定郑和的船队不会走得太远,他也只能枉把南洋作西洋,他也只能绘制出一张四平八稳平面无常的《航海图》。不可否认,郑和和他的船队,在已有的穿越风沙大漠的丝绸之路之外,又重新开辟出了另一条碧波万顷的海上丝绸之路,但实际上大明的禁海政策,尤其对民间的海上通商,从朱棣开始,就套牢着绳索。所谓的闭关锁国,并非从清朝开始,而是从大明早期就开始了。
说来,朱棣这人还是挺有意思,他净干大手笔的事。比如,他在他自己原先的燕王守地,豪建紫禁城,然后将都城迁移,天子戍边,气血满膛,威震北疆。比如,他命解缙、姚广孝等人主持编纂厚达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的《永乐大典》,而且不像后来的《四库全书》那样在收录文章时随意更改,而是对收录于此的古今七八千种图书做到了不删不减。比如,他下令铸造了一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重达46吨的青铜大钟,钟体内外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铸满了经文,当然这其中也有他自己潜心撰写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四十卷二十万言中的前二十卷十万字。这等于是朱棣把自己的得意文章,永久性地发表在了永乐大钟这块不朽的版面上。钟声一响就是90里,单是那尾音没有两三分钟根本停不下来。这么说来,他能派出郑和这样一支罕见规模的船队出访海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郑和船队的远行,之所以说收益没有后人寄想的那么大,首先是因为它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远行。用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等交换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都不过是一些附带性行为,甚至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也是附带性的。它的真正动因还是为了传播大明国威,建立和拓展朝贡体系,稳定外部秩序。从判断大明外部环境海晏河清的那一刻起,从陆权向海权过渡的最佳机会窗口便已经彻底关闭了,一代帝国从此满足和沉浸于朱元璋定制的“厚往薄来”的遗训之中,本该由此起步的海外贸易却被熄火。郑和船队曾经的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不过成为了孤帆远影。一方面是郑和下西洋,一方面是关键时期海洋却在中国近代史上严重缺位,竟这样矛盾地书写在我们的史书之中。
不能不说中国人是智慧的,好客的,但也不能不说中国人是单纯的,善良的。仿佛中国人总是会忽视和忘记,世界并不太平。直至从那时起500多年后,中国外交官仍然会发出痛彻心扉的感慨:“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在后明成祖和郑和时代,随着大明航海事业的人亡政息,辽阔的大洋海面眼睁睁地成为了西方国家纵横穿越的舞台,他们通过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并且也很快露出了他们坚船利炮的强盗本性。
世界在飞速变化,地缘在博弈,海上的争夺仍在继续,向空中的拓展也已完全展开。
平面的航海图已成久远的过去,新的课题已经到来。
或许,世界上最大的船是地球,世界上最大的海是星空。
钓 鱼
当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坐在渭河岸边用直钩钓鱼的时候,风平浪静之下,一场巨大风暴已经开始酝酿。
历史上的姜子牙确有其人,有据可查的子嗣众多。本属凡夫肉胎的他,却因超凡的智慧和功德,在当世叱咤风云,被后世捧为圣者。一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更是赋予了他封神的权力。他身披杏黄旗,手执打神鞭,成为不是神的神,成为比一般神还要阶高的神,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神。这也是东方神区别于西方神的一个明例,神既高高在上,但也朴实地生活在我们身边。姜子牙封神,不是宗教,不是迷信,是东方独有的文化形态。
但凡超人,必有超凡的举动。他的出场方式极为独特,也绝无仅有。选择用直钩钓鱼,正常人想不到,年轻人做不来,不仅渭河里的鱼不适应,整条渭河也不会搞明白。盘古开天以来,就没有人这么干过!不是疯人,却选择这种乖张行为,足以说明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垂钓。既然七十多年都已经隐忍了,此时的姜子牙肯定坐得住。我们能想象,当时高天上的流云如何倒映河中,远处的金戈铁马如何正在烧红历史的天空,社会缝隙中正是人仰马叫。只有胸中藏满风暴,脸上袒露从容的人,方才体现出高蹈者的气象。
帝辛并不知道自己将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身边人更不敢如实告诉他,外界早已为他送上“纣王”的侮号。因此,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无尚聪颖、口才好、气力大、智慧高的一派歌舞升平和欢乐祥和之中,都城朝歌的文娱生活已具相当水准。但当穷兵黩武、严刑峻法、酒池肉林这些词汇和他连结到一起的时候,显然他距离覆灭已经不远了。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无论东方历史、西方历史,还是古埃及的非洲历史,都总习惯在关键节点,找出一个女人来,很巧,妲己已没法推辞。只要她愿意以狐狸精的身份出现,历史会多少松口气,不用再担心传奇性和精彩度。历史是自己的,但更多时候,也是当事者和后继者共同创造的。
明白了这场钓鱼的背景,也就明白了姜子牙的用心。姜子牙并不是简单地坐在渭河边上,而是坐在岩浆欲要喷发的火山口上。姜子牙的鱼竿并不是简单地伸进了浑黄不清的渭河,而是伸进了一条波谲云诡的历史长河。周文王是鱼,周武王是鱼,商纣王是鱼,妲己也是鱼。因此,他轻轻一甩,鱼线就能从纣王和妲己的头顶上飞过去。他的抱负是钓出一个更理想的时代,他实现了。被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从此开启了又一个全新的文明进程。
三千多年过后,再未见一个敢于用直钩钓鱼的人。历史长河里真正的鱼并不是很多,姜子牙不得已,只能把自己变作一尾鱼,任凭后人钓过来,钓过去。
张世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学期刊社原社长、总编辑、《时代文学》主编,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作品见《收获》《人民文学》等知名文学期刊,《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海外文摘》《诗选刊》《小品文选刊》等多次选载,或入选年度选本。散文随笔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全国近百家报刊发表,获泰山文学奖、刘勰散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爱若微火》,作品集《牛背山情话》《古典的骨》《龙年笔记》《旧时光》《落叶飞花》《心雨》《张世勤文集》等多部。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嘉琪
责编:钟千惠
审核:吴雪倩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