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岁月丨我和收音机的流金岁月
我和收音机的流金岁月
□ 吴盛福
放暑假了,我回了趟老家。一进老屋,物是人非,睹物思人,徒增伤感。目之所及,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画面。尤其是那台收音机,勾起了我的回忆,回忆起我和收音机的流金岁月。
现在,家里若有一台收音机,那真可以算是一件古董了。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收音机,它是一本有声的书。我六七岁时,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那样的岁月,家里买了台收音机,算是买了大物件。这台收音机体形呈长方体,长约两尺,高和宽约一尺,底下四根大拇指粗,一寸来长的立柱,像踩着高跷。父亲还扯了块红布盖在收音机上,显得很喜庆。
每天早上,父亲的收音机如同闹钟,在雄壮的“歌唱祖国”音乐过后,“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了,我便自觉起床。我一边听着广播,一边扫地、洗茶杯、擦桌子,这是我每天早上的必修课。虽然我不懂那些天下大事,但我很崇拜那些播音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讲话。擦桌子,擦到收音机前,我止不住端详一会儿,这不就是个木匣子吗,怎么能说话呢?
母亲不赞成父亲买收音机,她说听收音机又不能当饭吃,但父亲坚持买回来了。为此,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母亲不赞成父亲买收音机的原因,不仅是买收音机要花钱,听的时候也要花钱。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所以听收音机要用电池。父亲买的收音机个头大,每个月要吃掉好几节电池。因此,我不敢独听收音机,那真是一种奢侈。
父亲总是在做事回家休息时,打开收音机给我听。上午收听的是“小喇叭”节目,小女孩一句稚气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随后是几声小喇叭,“嗒嘀嗒,嗒嘀嗒,嗒嗒……”我最喜欢听《西游记》中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一次,猪八戒去化斋,觅得一个西瓜,急不可待地把西瓜一切四瓣,先把自己的那一瓣如风卷残云般地吃了,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第二块西瓜,嘟囔了一句“沙师弟,我替你吃了吧”。吃完了沙师弟的,接着当然是替猴哥吃了。最后,只剩下留给师傅的那块西瓜。猪八戒着实犹豫了一下,他心中是有师傅的,但他还是管不住贪吃的那张嘴。讲故事的是名老者,他用沧桑而又雄浑的嗓音把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塑造得栩栩如生,令人捧腹。
下午听的多是“星星火炬”,一名少年穿越丛林,追寻大象的足迹,与偷猎者斗智斗勇。我的心一路追随着少年,仿佛身临其境,有时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有时对偷猎者恨得直咬牙。
父亲喜欢听评书,我也喜欢听。我家离学校有三四里路,每天中午放了学,我一路跑回家,准时坐在收音机旁。火烧赤壁、大战裴元庆、三打祝家庄……随着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表演艺术家的精彩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紧扣住我的心弦,一个个英雄形象深深烙进了我的灵魂。
田地分产到户后,放了暑假,我便如同加入了生产队。那时候,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全民皆兵参加劳动,移秧、插秧、耘田、锄棉花草……
那时的农产品几乎都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个暑假要耘四五次稻田,为红薯、芝麻锄两三次草,棉花草几乎每个星期要锄一次,下雨天就打伞蹲在地上拔草。尤其是“双抢”(抢收、抢栽),那真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挥汗如雨、汗流浃背……我现在几乎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记忆中“双抢”的辛苦情状。
父亲则把收音机带到田间地头,新闻、歌曲、广播剧……收音机为我们报时,催我们收工,缓解了我们的疲惫,给予了我们些许慰藉,陪着我们度过那段悠悠的艰苦岁月。
上了师范,叔叔送给我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有一天,下了晚自习,我躺在床上听收音机,被来查寝的班主任逮住,罚我第二天在全班同学面前作检讨。我当时并不知道不能在寝室听收音机。唉,从此,我与收音机分道扬镳了。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家三十多公里的一所中心小学,担任辅导员,负责广播站。广播室也是我的卧室,一台燕舞牌收录机、一个高音喇叭、一个话筒、几盒录音带,这就是广播站的全部家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收音机已改名叫收录机了。现在看来,那广播站条件甚是简陋,但在当时算是得天独厚了。那时,交通不便,一个月工资微薄,也舍不得多花钱在路费上,常常是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在那些单身的日子里,我常常以书为伴,或是躺在床上听着收录机,听着一首首动听的旋律,直到夜半更深。
如今,父母已经作古,收音机也已日渐式微,但它讲的故事我依然耳熟能详,那些熟悉的旋律时常萦绕在我的耳旁。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文婧
责编:钟千惠
审核:朱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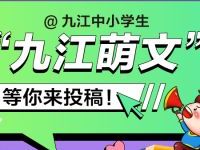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