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丨(品读)蒿草青青处 烟火照归程

蒿草青青处 烟火照归程
■ 桂孝树
初捧付鹤鸣先生的新作《蒿草青青》,指尖触碰到封面那抹湿润的青绿,仿佛能嗅到幕阜山间蒿草混着泥土的气息。这部以“蒿”为魂的文集,用九个篇章将故乡的山河草木、人情旧事织成一幅流动的乡土画卷。当城市的霓虹模糊了归乡的路,书中那些沾着露水的文字,正以最朴素的方式,叩击着每个漂泊者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蒿草为引:自然与乡愁的同频共振
在《蒿景》篇中,作者笔下的幕阜山不是被滤镜美化的风景,而是活在四季轮回里的生命场域。春日白鹤坪的蒿草“青葱嫩绿”,是可以攥在手心的生机;夏日修江河畔的“森林氧吧”,扳罾的竹篙搅碎河面的金光;秋日辽山顶的风掠过蒿草,将百里修河的轮廓吹成水墨画;冬日蒿草在雪地里蛰伏,像极了故乡人沉默却坚韧的脊梁。
这种对自然的书写,绝非简单的景物描摹。当作者“钻进桂竹丛拔春笋”“坐在水边独饮醉在东岭”,自然万物早已与生活仪式融为一体。就像蒿草既是可食的野菜,也是编织记忆的线索——阿婶织的小蛋兜盛着童年的清明,二叔家张屠户“劁猪”的吆喝惊飞了檐下的燕子,父亲锄地的背影与牛群在田垄间构成黑白剪影。这些细节让我想起自己故乡的槐树。每逢五月开花时,奶奶总会用笸箩收一捧花瓣蒸糕,食物的香气里,永远藏着土地对人的馈赠。
作者对蒿的偏爱,恰似沈从文对湘西的眷恋。蒿草在书中不仅是地理符号,更是精神原乡的图腾。当他站在辽山顶眺望修河,“想起手写的妻与初相识的日子”,错发的短信里藏着被时光稀释的温柔;在五月汨罗想起阿婶,“娭毑娘”与“胞衣场”的称谓里,是血脉传承的隐秘密码。自然景物与人文情感的交织,让乡愁有了可触可感的形态——它是蒿草叶上的露珠,是修河滩的歌谣,是老木匠手中渐成雏形的木具。
蒿庐为基:乡土记忆的考古与重构
《蒿庐》篇像一座露天博物馆,陈列着故乡的千年往事与市井烟火。从船滩老街的温泉旧事到修河滩歌,从明朝大将胡大海到梅友支部的油灯,作者以考据般的耐心,打捞被岁月掩埋的碎片。当他说起“小汉口”船滩的美食,那道被称为史上最“恶毒”的佳肴,实则是穷乡僻壤里人们对滋味的极致追求;坎头村的来历与降仙坡的传说,让地理名词成为神话叙事的注脚;而永济桥上辽山寨的故事,又让现实的石桥化作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
这种书写让我想起汪曾祺对故乡食物的描摹,看似琐碎的日常,实则是文化基因的延续。比如作者写“三大件”“拆空调”等生活片段,表面是物质变迁史,内里却是乡村伦理的演变——分家时的争执、退票时的窘迫、补胎时的算计,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真实地记录着时代烙印。尤其当他提到“银手镯”与“吝啬鬼”,那些被传统道德审视的人与事,在作者笔下却多了份理解的温情:乡土社会的“抠”,何尝不是对资源匮乏的生存智慧?
最动人的是对宗族文化的书写。石坑傅家的“球场‘十一仲’”与“赖罗体一家亲”,将姓氏祠堂转化为情感共同体;太平山祖师爷张道清与黄庭坚的渊源,则让自然山水有了人文厚度。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故乡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由血缘、传说、习俗共同构筑的精神城堡。当城市里的我们对着族谱只剩陌生的姓氏,书中那盏“一直亮着”的灯,分明是照亮文化根系的火种。
蒿烟为魂:人间烟火里的众生相
《蒿烟》篇是一曲故乡的众生颂,二十二篇短文里,有苦菜草般坚韧的普通人,有小黄牛般憨厚的乡邻,也有讨债、退彩礼等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切片。那个搜集修河滩歌900余首的刘老师,像极了民间文化的守望者;“活党史”开宁老人是村民心中的灯,照亮被遗忘的岁月;“辽山歌王”方由根的嗓子里,藏着山歌调式的基因密码。
作者的笔触始终带着悲悯的温度。写“一对野鸳鸯的发财梦”,没有批判投机取巧,而是看见底层人对命运的不甘;写“扫盲班里的鲜事”,那些握着铅笔的粗糙手掌,分明在书写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甚至连“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戏文,在船滩方言的演绎中,也成了乡土智慧的另类表达。这种书写让我想起老舍笔下的北平,每个小人物都是时代的主角,他们的悲欢离合,构成了社会的肌理。
特别喜欢《红楼梦》与船滩方言三百条的跨界书写。当曹雪芹的文字遇上赣西北的乡音,“端茶倒水”变成“递茶过盏”,“吝啬”说成“夹壳”,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作者对语言的敏感,让我想起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当我们失去方言,失去的或许是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视角。
蒿语为信:时光里的自我对话
《蒿评》与《蒿音》篇像作者的心灵独白。七篇读后感里,修水库的移民经历让“胞衣场”成为朱砂痣般的牵挂;读《水车谣》时,“水花永远开在深情的小巷”的喟叹,是对流逝时光的挽留。而《蒿音》里对女性、法律、道德评议会的思考,则让乡土叙事有了现代性的维度——当作者呼吁“让妻子存些私房钱”,当他探讨“林权纠纷调处四字诀”,字里行间是对故乡发展的拳拳之心。
这种自我对话最动人的,是贯穿全书的生长意识。《蒿土》篇中,从1996年到2024年的文字,作者坦然承认“早年幼稚,如今平淡”,但恰恰是这种真实,让文字有了生长的痕迹。就像春天的蒿草,从拔苦菜、掐蕨到“开秧门”,生命的循环里藏着对时光的敬畏。当他写“偷得海棠三分白,四月雨生烟”,当他在“蒿里人家”看杨柳依依、写《船滩赋》,个体生命与故乡山水早已互为镜像。
《蒿语》篇里的四篇文字,藏着作者与笔墨打交道的半生情缘。当他提及自己担任7年《船滩》执行主编的经历,那句“办刊如做人”道尽了纸页间的甘苦——铅字排版的日夜,何尝不是在打磨对乡土的赤子之心?数十年报社、电台通讯员的生涯,让报刊的墨香、质朴和厚重,都成了刻进骨髓的“媒体基因”。
最动人的是他寻找旧作时的怅然:“找了几次都没找到,只有明月知我心。”那些散佚的文字,或许早已化作修河的浪花,在时光里奔涌成西海平湖。他的字里行间分明有未灭的灯盏,就像修河永远记得每滴河水的来路,那些与文字纠缠的岁月,早已在灵魂深处长成了蒿草般坚韧的印记。
这哪里是写媒体生涯,分明是用墨香编织的精神家谱。当我们在数字时代轻触屏幕,这些带着铅字温度的回忆,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提醒着:真正的文字,从来不在泛黄的纸页里,而在那些为热爱奔走过的日夜中,在明月与河流永恒的注视里。
合上书页,窗外城市的灯火正浓,而书中的蒿草仍在幕阜山间疯长。付鹤鸣先生用文字搭建的蒿草世界,不是逃避现实的田园牧歌,而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视——那里有落后与进步的撕扯,有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但更多的是像蒿草一样扎根土地的坚韧,是像修河水一样奔涌不息的生命力。
在这个被数字洪流裹挟的时代,我们或许都需要这样一本蒿草之书:让它的青绿驱散城市的灰蒙,让它的烟火气温暖漂泊的灵魂。因为无论走多远,故乡的蒿草永远在记忆里青青,等着每个归人,在草木芬芳中,找回失落的来处与归途。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925488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文婧
责编:肖文翔
审核:杨春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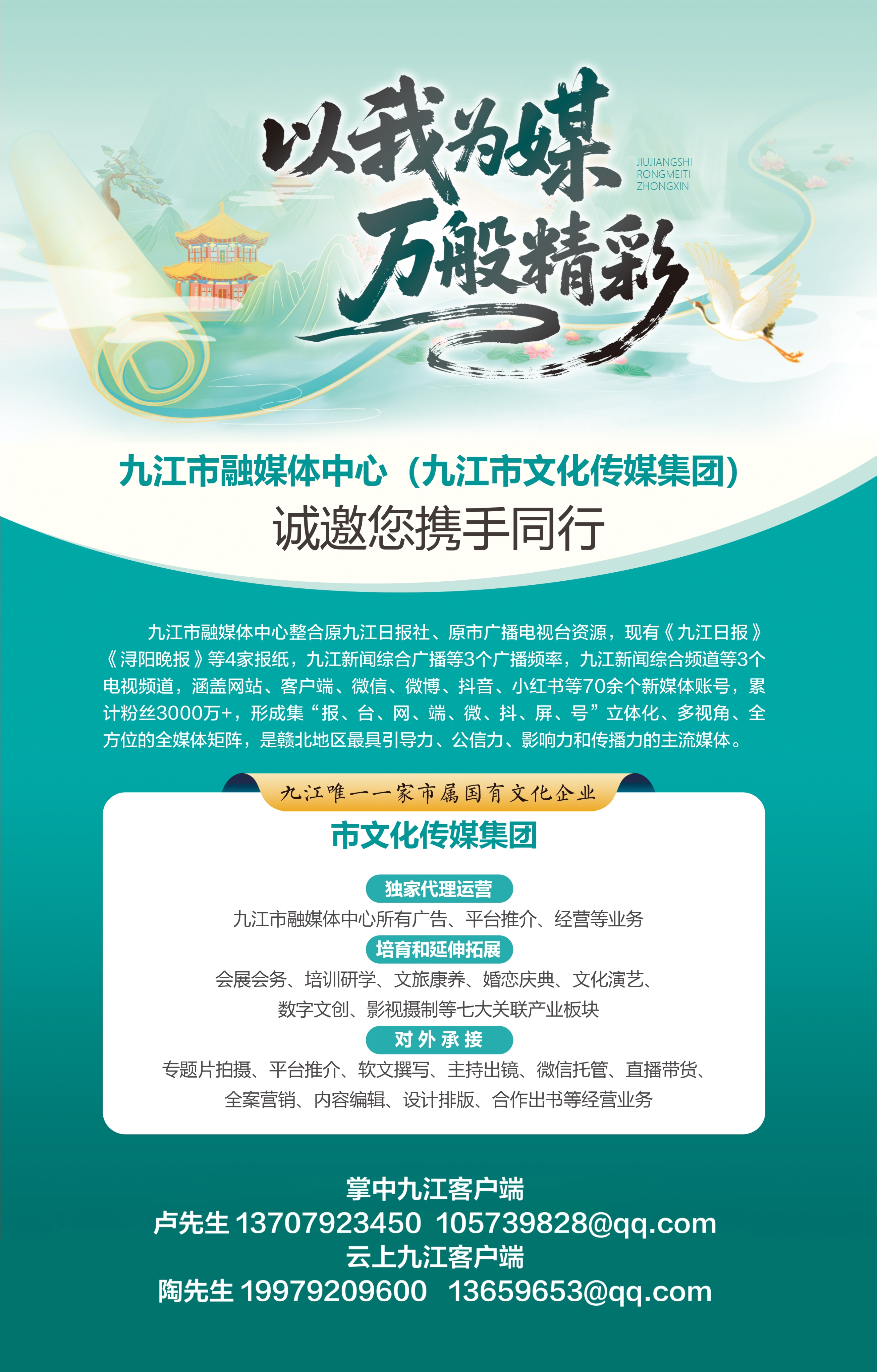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