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丨小屋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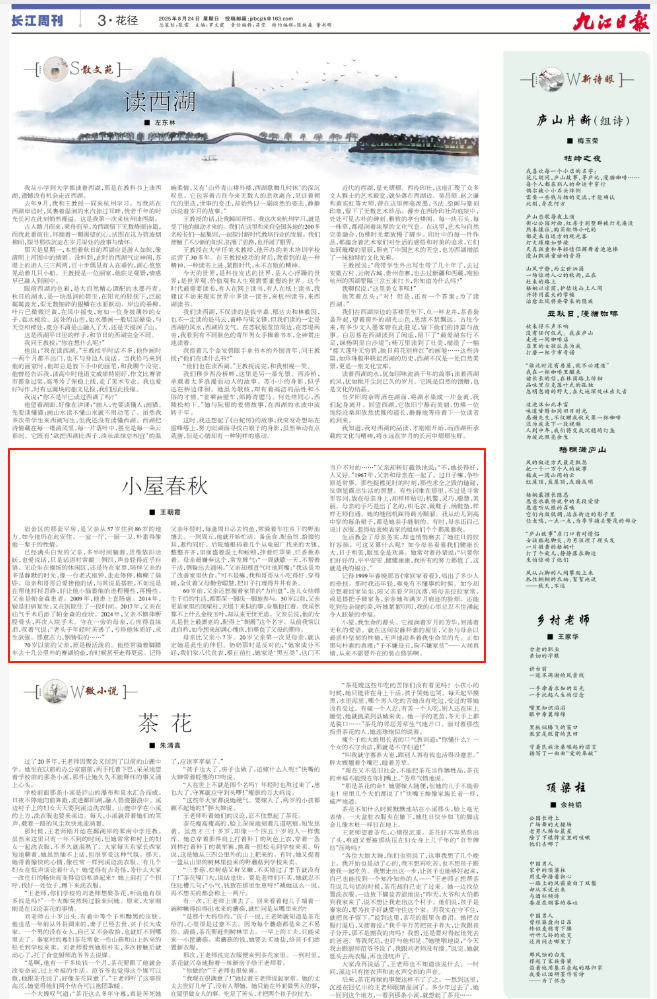
■ 王朝霞
宿舍区的那套平房,是父亲从57岁住到86岁的地方,如今他仍在此安住。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朴素得像他一辈子的性情。
已经满头白发的父亲,多半时间躺着,思维依旧活跃,也爱说话,只是话语时常颠三倒四,声音轻得近乎自语。无论坐在操场的休闲区,还是待在家里,陪伴父亲的多是静默的时光,像一台老式座钟,走走停停,模糊了晨昏。母亲和哥哥总爱接他的话,与其说是搭腔,不如说是在帮他捋捋思路,好让他小脑萎缩的进程慢些,再慢些。父亲是帕金森患者。2009年,他患上直肠癌。2014年,疑是旧病复发,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2017年,父亲在疝气手术后添了帕金森的症状。2024年,父亲不慎摔断股骨头,再次入院手术。守在一旁的母亲,心疼得直抹泪,叹着气说:“老头子年轻时苦透了,亏得他体质好,求生欲强。那意志力,钢铸似的……”
70岁以前的父亲,原是极活泼的。他经常骑着脚踏车去十几公里外的赛湖钓鱼,有时候甚至走得更远。记得父亲年轻时,每逢周日必去钓鱼,常骑着车往乡下的野池塘去。一到周五,他就开始忙活。备鱼食、配鱼饵、拾掇钓具,邀约同好。后院墙根码着几个从电磁厂找来的大钵,整整齐齐,里面盛着湿土和蚯蚓,拌着烂苹果、烂香蕉养着。母亲最嫌弃这个,常发脾气:“一周就歇一天,不帮着干活,倒躲出去清闲。”父亲却理直气壮地回嘴:“我这是为了改善家里伙食。”可不是嘛,我和哥哥从小吃得好、穿得暖,全仗着父母勤劳聪慧,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
60岁前,父亲还想握着家里的“方向盘”,连儿女结婚生子后的生活,都要深一脚浅一脚地参与。50岁以前,父亲更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塌下来似的事,全靠他扛着。我虽然算不上什么金枝玉叶,却从来无忧无虑。父亲总说,他的女儿是世上最漂亮的,配得上“朝霞”这个名字。从前我常以此自矜,如今想来却满心愧疚,怕辜负了父母的期待。
母亲比父亲小7岁。20岁父亲第一次见母亲,就认定她是此生的伴侣。奶奶那时是反对的,“她家成分不好,我们家八代贫农,根正苗红,她家是‘黑五类’,这门不当户不对的……”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不,她长得好,人又好。”1967年,父亲和母亲在一起了。过日子嘛,争吵原是常事。那些捉襟见肘的时刻,那些求全之毁的磕碰,反倒显露出生活的智慧。有些词堆在那里,不过是寻常形容词,放在母亲身上,却样样贴切:机警、灵巧、聪慧、美丽。母亲的手巧是出了名的,织毛衣、做鞋子、纳鞋垫,样样无师自通。她的缝纫机踩得最为顺溜。我从幼儿到高中穿的每条裙子,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有时,母亲还自己设计衣服,惹得姑表姨表家的姐妹们个个都羡慕我。
生活教会了母亲务实,却也悄悄磨去了她往日的姣好容颜。可这又算什么呢?如今母亲看着我们健康长大,日子和美,眼里全是欢喜。她常对着孙辈说:“只要你们好好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所有的努力都值了,这就是我的福分。”
记得1999年春晚那首《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多少人的牵挂。那时我还年轻,难免有不懂事的时候。如今却总想着回家坐坐,陪父亲看夕阳沉落,陪母亲拉拉家常,或是搭把手做家务,亲亲她布满岁月痕迹的脸颊。还能吃到母亲烧的菜,听她絮絮叨叨,我的心里总忍不住涌起令人眩晕的幸福。
小屋,我生命的源头。它浸润着岁月的芳华,回荡着无私的爱语。就在这间安静朴素的屋里,父亲与母亲以最质朴坚韧的性情,无声地滋养着我生命里的光。正如那句朴素的真理:“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人间真情,从来不需要外在的装点修饰啊。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925488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嘉琪
责编:肖文翔
审核:熊焕唐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