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丨(散文苑)不锈的烟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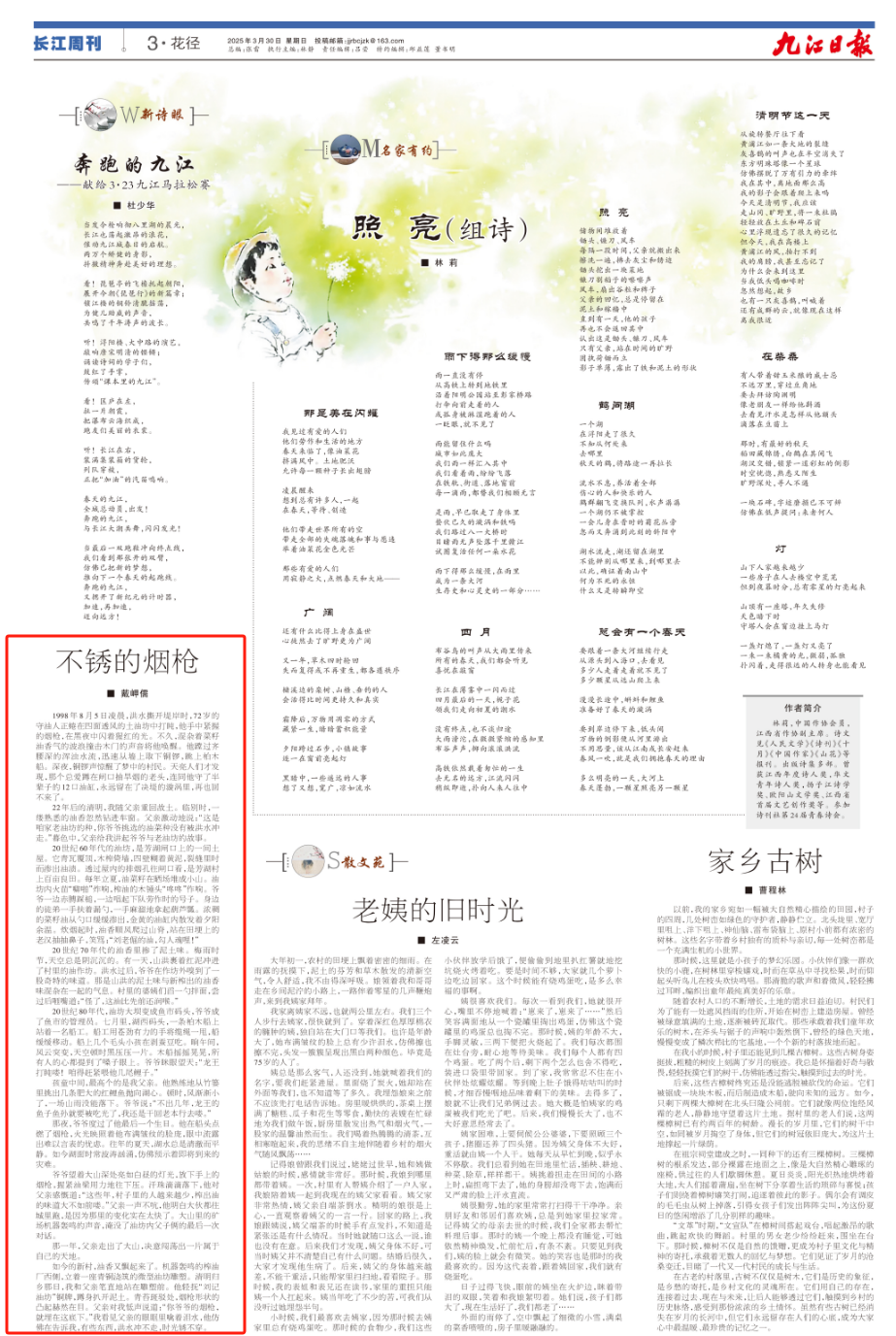
不锈的烟枪
■ 戴岬儒
1998年8月5日凌晨,洪水撕开堤岸时,72岁的守油人正蜷在四面透风的土油坊中打盹,他手中紧握的烟枪,在黑夜中闪着猩红的光。不久,混杂着菜籽油香气的波浪撞击木门的声音将他唤醒。他蹚过齐腰深的浑浊水流,迅速从墙上取下铜锣,跳上屋角的柏木船。深夜,铜锣声惊醒了梦中的所有村民。天亮人们才发现,那个总爱蹲在闸口抽旱烟的老头,连同他守了半辈子的12口油缸,永远留在了决堤的漩涡里,再也回不来了。
22年后的清明,我随父亲重回故土。临别时,一缕熟悉的油香忽然钻进车窗。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咱家老油坊的种,你爷爷挑选的油菜种没有被洪水冲走。”暮色中,父亲给我讲起爷爷与老油坊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的油坊,是芳湖闸口上的一间土屋。它青瓦覆顶,木榨倚墙,四壁糊着黄泥,裂缝里时而渗出油渍。透过屋内的排烟孔往闸口看,是芳湖村上百亩良田。每年立夏,油菜籽在晒场堆成小山。油坊内火苗“噼啪”炸响,榨油的木锤头“咚咚”作响。爷爷一边赤膊踩槌,一边唱起下队劳作时的号子。身边的徒弟一手扶着漏勺,一手麻溜地拿起葫芦瓢。浓稠的菜籽油从勺口缓缓渗出,金黄的油缸内散发着夕阳余温。炊烟起时,油香顺风爬过山脊,站在田埂上的老汉抽抽鼻子,笑骂:“刘老倔的油,勾人魂哩!”
20世纪70年代的油香里掺了泥土味。梅雨时节,天空总是阴沉沉的。有一天,山洪裹着红泥冲进了村里的油作坊。洪水过后,爷爷在作坊外嗅到了一股奇特的味道。那是山洪的泥土味与新榨出的油香味混杂在一起的气息。村里的婆姨们舀一勺拌面,尝过后咂嘴道:“怪了,这油比先前还润喉。”
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喜欢鱼腥味胜过油香味,油坊大坝变成鱼市码头,爷爷成了鱼市的管理员。七月里,湖西码头,一条柏木船上站着一名船工。船工用苍劲有力的手将缆绳一甩,船缓缓移动。船上几个毛头小孩在剥蚕豆吃。晌午间,风云突变,天空顿时黑压压一片。木船摇摇晃晃,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爷爷眯眼望天:“龙王打盹喽!咱得赶紧喂他几尾鲤子。”
孩童中间,最高个的是我父亲。他熟练地从竹篓里挑出几条肥大的红鲤鱼抛向湖心。顿时,风渐渐小了,一场山雨没能落下。爷爷说:“不出几年,龙王的鱼子鱼孙就要被吃光了,我还是干回老本行去喽。”
那夜,爷爷度过了他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个生日。他在船头点燃了烟枪,火光映照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庞,眼中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忧虑。往年的夏天,湖水总是清澈而平静。如今湖面时常波涛汹涌,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
爷爷望着大山深处亮如白昼的灯光,放下手上的烟枪,握紧油梁用力地往下压。汗珠滴滴落下,他对父亲感慨道:“这些年,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榨出油的味道大不如前喽。”父亲一声不吭,他明白大伙都往城里跑,是因为那里的变化实在太快了。大山里的矿场机器轰鸣的声音,淹没了油坊内父子俩的最后一次对话。
那一年,父亲走出了大山,决意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如今的新村,油香又飘起来了。机器轰鸣的榨油厂西侧,立着一座青铜浇筑的微型油坊。清明归乡那日,我和父亲笔直地站在模型前。他轻抚“刘记油坊”铜牌,蹲身扒开泥土。青苔斑驳处,烟枪形状的凸起赫然在目。父亲对我低声说道:“你爷爷的烟枪,就埋在这底下。”我看见父亲的眼眶里噙着泪水,他仿佛在告诉我,有些东西,洪水冲不走,时光锈不穿。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文婧
责编:肖文翔
审核:杨春霞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