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 | (讲述)茅山头轶事

茅山头轶事
■ 邓星明
1968年8月28日,九江各中学几千人下放茅山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刚下放茅山头,我被分配到五连(螺丝墩),按照当时的要求,每天6时起床“早敬”,如迟到或不虔诚,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然后列队操练跑步。
吃完早饭后,大家由老农带领下地劳作。我们这批城市长大的孩子,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6岁,猛然间得像农民一样头顶烈日、脚踏黄土劳作,谁能吃得消。但谁也不敢叫苦,许多女孩子只能晚上偷偷地在被窝里哭泣。
螺丝墩的土壤肥不足,必须到九江城里去找粪便。两人一辆粪车,到城里去拉粪,半天时间拉回就可以完成工作量。后来大家都喜欢去拖粪,因为出外拖粪相对自由。后来因各连都缺肥料,大家都去九江城区拖粪,以致各连各队展开了一场“抢粪大战”,大家常为抢粪起冲突。现在听来十分好笑,当时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下放一个多月之后,知青们渐渐明白了自己就是一个农民。晚饭之后,我们几个知青好友坐在八里湖大堤上,遥望着十里河对岸的九江城区。看着车水马龙的街市及熙熙攘攘的市民,大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我们这批孩子在城里长大,此时突然羡慕起城里人了。那时候,我们的户口已由城市转为农村。
几个同学纷纷感慨:“以前天天在城里,觉得无聊,现在突然怀念起过去的日子。”
“我们还能回去吗?”
“从城里户口转到茅山头很容易,再转回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了。”
“还想回去,别做梦了!准备当一辈子农民吧!”
……
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里,螺丝墩的那段生活十分压抑。大家每天都在苦闷彷徨、提心吊胆中度日如年。
我大概在螺丝墩待了几个月,就接到总场传来的消息,因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被调到离总场最近的七连。茅山头宣传队是个动态集体,进出频繁。宣传队成员都是有点文艺特长的知青,带队干部和蔼可亲,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集体。
后来,陆续从茅山头宣传队走进专业剧团的有10人,大多数成为各单位的文艺骨干。值得一提的是罗艺锋,他后来成为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没有念过大学而担任大学校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茅山头宣传队由于实力雄厚,充满生气活力,很快打出了名气。九江遇到有重大庆祝活动,就会邀请我们前去演出。
当时这里没有客车,我们出外演出坐得最好的汽车就是解放牌大货车。若解放牌货车出外拉货,就会派拖拉机过来接我们。有时候,拖拉机刚拖完牛粪,没清洗干净。我们上去后,身上沾了不少牛粪味。到演出场所,还没进会场,观众远远地就闻到牛粪味,纷纷说:“茅山头的来了!茅山头的来了!”
我们宣传队开场式一般由周青秋和舒梅仙负责。他们两人学过武功,每次都从幕内疾步冲上台,一连几个鹞子翻身后,用一个劈叉漂亮地亮相。我们的歌曲《向阳姑娘就是强》、舞蹈《美丽的壮景》、笛子独奏《苗岭的早晨》、群口词《战天斗地英雄汉》、独唱《沁园春·雪》等节目,都深受群众喜爱。表演结束后,观众如雷般的掌声既是对茅山头宣传队节目的肯定,也有对我们这些知青的支持。
宣传队到市里演出,总场会派车送去,但从不派车接回去。当年没有公交车,我们只能走回来。从市人民剧院,经过向阳闸,走到总场有近十公里地,大家手里还要拿着乐器、道具、服装等物件。好在当时大家年轻,也不以为苦。
茅山头的“干道”没有路灯,我们每次回来都是摸索着前行。刚开始,大家没经验,遇到雨后总往亮处走,每每都踩到一脚的水。后来才知道,下雨过后要往黑处走,那才是干地。
宣传队没有排练场地,只能在食堂饭厅排练。有一次,我们5个男演员排练《群口词》时很不顺利。轮到我和张伟民表演时,我们的声音颤抖,语不连贯,还常常忘词。大家都很奇怪。一个姓杨的演员无意间碰到我的手臂,吃惊道:“哎呀,你的手怎么这样烫呀?是不是发烧?”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俩送到医务室,医生一量体温,发现我烧到了39.5度,张伟民烧到了40度。医生说我们发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听见医生的诊断,我顿时瘫倒,浑身没力气,回到宿舍后,盖几床棉被都冷。
宣传队并不是一年到头都排练演出,有宣传任务就抽上来,平时就回基层,由老农带着下地干活。记得我分到七连二排,排长叫余蛟龙,是一个和善的中年男子。
有一次,余排长安排我和几个知青翻垦一块红花草地。这里的蛇特别多,大都是金环蛇和银环蛇。平时,我们听说哪里有蛇,都躲得远远的。可现在要劳作,躲不了。好在我们人多,每人手里有铁锹,只要有人喊:“这里有蛇!”大家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用铁锹乱打一气。后来,大家的胆子越来越大,不但不会轻易把蛇打死,还敢把蛇尾巴拎起来甩玩。玩够了,再乱棍打死。有一次,我们把打死的蛇放在田埂上,一上午竟打死7条蛇,每条都有1米多长。
后来有人提议,丢掉太可惜,可以弄来吃。于是,我和陈立行找来一把刀,就在田埂上杀蛇剥皮。这也是我第一次杀蛇剥蛇。我曾听说“杀蛇杀七寸”,于是,离蛇头七寸部位我都没要。大家都听说过蛇胆能明目,每取出一个蛇胆,都有人当场吞服了。
回到宿舍后,我们找有锅灶的人家,准备一些佐料,把七条蛇全部红烧,装了满满一脸盆,香气扑鼻。有人还去小卖铺买了瓶白酒,大家围坐一起吃吃喝喝。
一天,听人说,有只黄鼠狼掉到食堂水池淹死了。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果然有只死得硬邦邦的黄鼠狼。食堂的人准备丢掉,我们舍不得,将黄鼠狼要了回来。尝过蛇肉的鲜美,这次,我们又想尝尝黄鼠狼的味道。我又与陈立行合作,把黄鼠狼挂在宿舍门后钉子上,从颈部开刀,试着剥皮。开始还顺利,从颈部一直剥到了尾巴。谁知屁眼处一刀下去,一股强烈骚味喷了出来,那种从未闻过的骚味熏得我们脑子发晕,眼睛都睁不开。吓得我们一个个夺门而逃。在外面转悠了几个小时后,才小心翼翼地进房去,把黄鼠狼扔进了垃圾桶。
茅山头曾被戏称为“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茅山头属红色黏性土壤,天晴时地面结块,非常坚硬。一遇到下雨,就变成了泥浆,粘性很强。在茅山头,雨靴是人们劳动和生活必备用品。
那时我没有雨靴,仅有两双解放牌球鞋换洗着穿。我一直非常渴望有双雨靴。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16元。父亲和大弟下放修水,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每月发工资后,要给家里寄去6元,补贴家用。当时,我跑遍了九江各大百货商场,最便宜的一双雨靴也需要6.2元。我几个月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存够了钱,狠心买了一双短筒雨靴。那年我20岁,尚有爱美之心,穿着崭新雨靴,心里美滋滋的。每天劳动完了,我都把雨靴擦得油光发亮,特别爱惜。
好景不长,我的雨靴才穿了5天,就不翼而飞,急得我到处寻找。我找遍所有可能丢失的地方,一无所获后,这才意识到可能被人偷走了。我伤心极了,一心想找回雨靴。从丢雨靴那天起,凡是下雨天,我都留意周边所有穿新雨靴的人。许多知道我丢雨靴的同学纷纷安慰我,积极地帮我四处打听,想帮我找回来。
有一天,四连的俞小屏传来消息,说他们连里最近有人穿新雨靴。我连忙赶过去,找到那个小伙子。可小伙子一口咬定雨靴是他自己买的,我没办法,只得作罢。
住在我上铺的周金水有两双雨靴。遇到下雨时,他把其中一双雨靴借给我穿了十几天。50年后,回想这件事,我仍感慨不已。
茅山头是血吸虫疫区,垦殖场每年都要给职工开展普查活动。1969年的普查中,我被确定为血吸虫患者。血吸虫在茅山头是常见病,许多人全家都患上了。当时,与我同时检查出来的患病者有一百多人。我们被安排在茅山头医务所住院治疗。我住的小病房有两张病床,同房是个带队干部,叫殷敏如。他是江西农学院文革前的大学生,二十多岁,干部编制,月工资有42元。
20多天住院期间,我们朝夕相处,成了好朋友。当年治疗血吸虫病,主要方法就是打锑剂,一共20针。每天一针,静脉注射。每天清晨6时,医护人员查房,量血压测体温,接着就是静脉注射,大概需要一上午时间。锑剂是种含毒药物,既杀死血吸虫,对肝胆也有损害。一般人打到十几针时,会出现头晕呕吐乏力等症状。我当时年轻,反应还算轻的。打到17针时,身体才有些反应,停了一天。
打完针,我们可以在家休息一周。我到八连(奶牛场),找到朋友买鸡补身体。我连吃两只鸡,脸色才有点红润。
50多年前的茅山头,在六连与七连之间有条向阳河,河水常年流动,水质清澈。河上有座水泥桥,叫向阳桥。那年头茅山头没有自来水,吃的是井水,用的是向阳河的水。茅山人天天参加繁重体力劳动,免不了要洗澡洗衣服,向阳河就成了知青天然的澡堂和洗衣场所。
一天,劳动之后,宣传队男同胞到向阳河洗澡。队长徐建南别出心裁地说,当天所有下水的人,必须从向阳桥上跳下来。桥面与水面至少也有三四米,许多人胆怯不敢跳,也有几个胆大的先跳了。男人嘛,都讲脸面,不想被同伴看作胆小鬼。在徐建南的忽悠下,每人都从桥上跳了下去。当然,大家没有什么漂亮姿势,大都是“冰棍式”,也就是双手双脚并拢,闭着眼睛,直直往下跳。好在水很深,大家会游泳,没出什么意外。
当时向阳河有许多鱼,桥底小鱼苗很多。徐建南又出馊主意:“今天每人要生吃一条小鱼,否则不准上岸。”说着他自己抓一条鱼苗,在大家的见证下,放进嘴里吃完了。徐建南吃完鱼苗之后,大家只好一个个抓鱼苗吃。我第一次吃生鱼,只觉得鱼苗放进嘴里还动了一下。我用牙齿胡乱咬碎后就囫囵吞枣地咽了下去,除了觉得有股腥味外也没什么特殊感觉。每人吃完还要张开嘴让大家看看,引来一阵阵笑声和欢呼声。
在茅山头的日子里,我们都沾了不少野性。大家的胆子大了,举止放开了,敢打蛇,敢吃生鱼,从地里拔个萝卜在衣服上擦几下就能直接啃……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浑身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在繁重劳动之后,回归自然,寻找欢乐,是年轻人的天性。向阳河是我们茅山知青快乐的发源地,直到现在,大家提起向阳河,都十分怀念。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925488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吴晨
责编:肖文翔
审核:吴雪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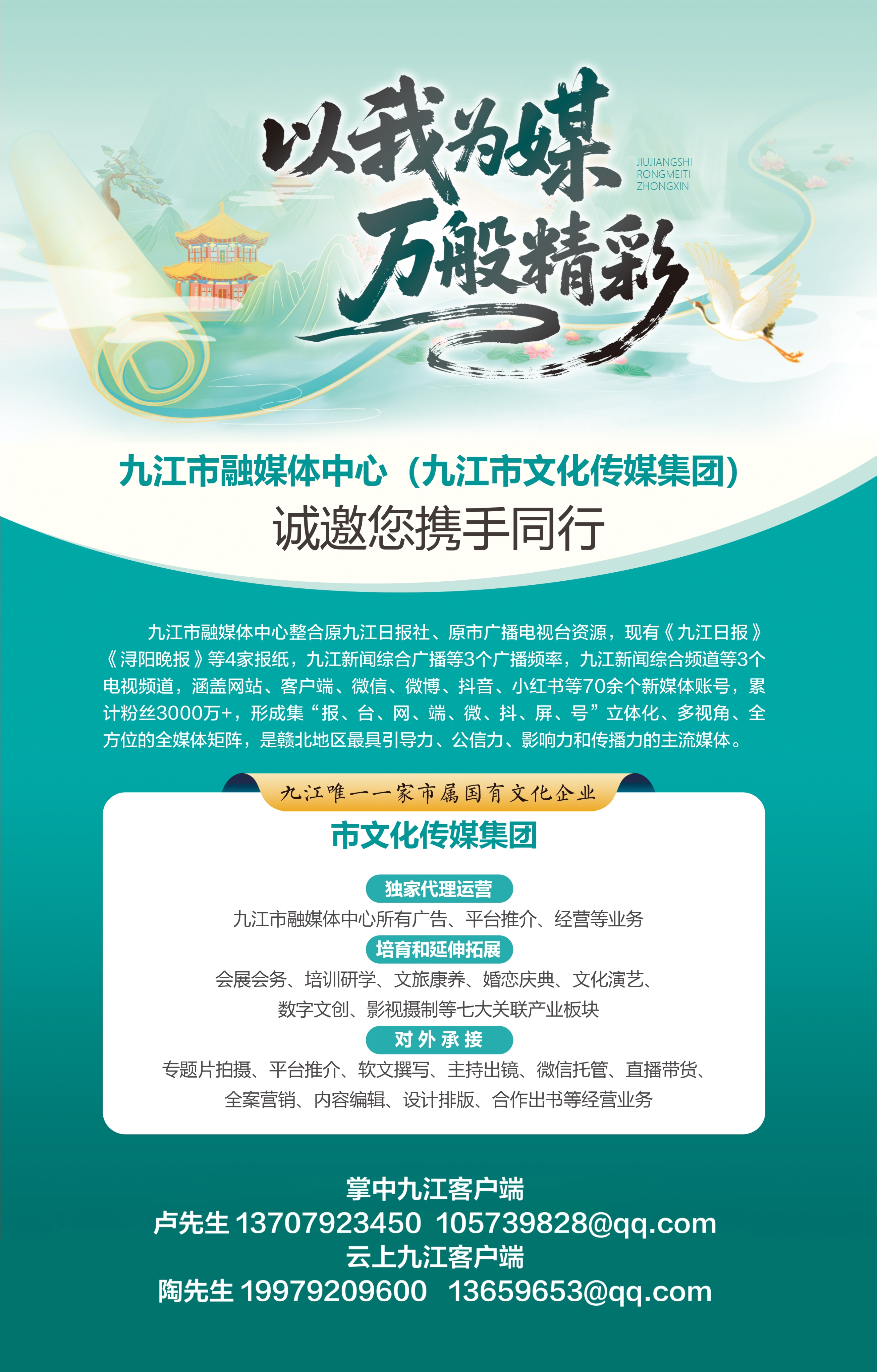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