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九江丨(讲述)孩童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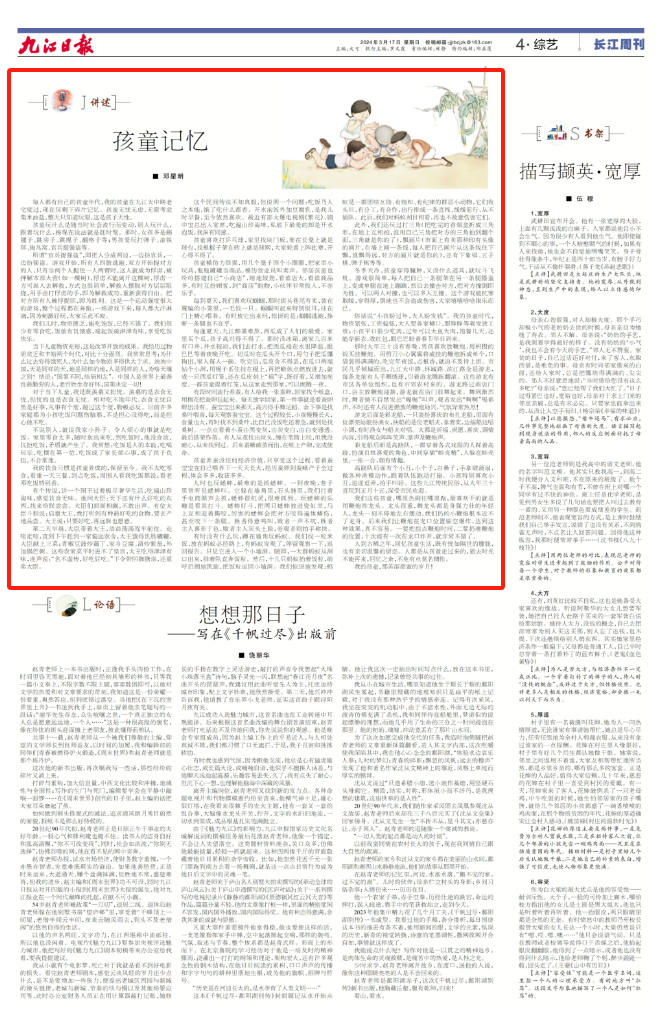
孩童记忆
■ 邓星明
每人都有自己的孩童年代,我的孩童在九江大中路老宅度过,现在仅剩下碎片记忆。孩童无忧无虑,无需考虑柴米油盐,整天只知道玩耍,这是孩子天性。
孩童玩什么是随当时社会流行而变动,别人玩什么,跟着玩什么,按现在说法就是赶时髦。那时,女孩多是踢毽子、跳房子、跳绳子、翻格子等;男孩爱玩打弹子、滚铁环、掏鸟窝、官兵捉强盗等。
所谓“官兵捉强盗”,即把人分成两边,一边扮官兵,一边扮强盗。游戏开始,所有人四散逃跑,双方开始捉对方的人,只有当两个人捉住一人两臂时,这人就成为俘虏,被押解本部大营(如一棵树),俘虏不能离开这棵树,俘虏一方可派人去解救,方式也很简单,解救人摆脱对方层层阻挠,用手击打俘虏的手,即为解救成功,重新获得自由。把对方所有人被俘捉回,即为胜利。这是一个运动强度很大的游戏,整个过程都在奔跑,一场游戏下来,每人都大汗淋漓,因为刺激好玩,大家乐此不疲。
我们儿时,物资匮乏,能吃饱饭,已经不错了。我们很少有零食吃,饭前有饥饿感,端起饭碗津津有味,享受吃饭快乐。
当下儿童物资充裕,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经历过物质贫乏和丰裕两个时代,对比十分强烈。我常常思考:为什么过去穷得饿死人,为什么如今物质多得供大于求。泱泱中国,天是同样的天,地是同样的地,人是同样的人,为啥天壤之别?结论:“国策不同,结局相左”。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勤劳的人,老百姓生存好坏,国策决定一切!
对于当下儿童,我是既羡慕又担忧。羡慕的是衣食无忧,担忧的也是衣食无忧。相对吃不饱年代,衣食无忧自然是好事,凡事有个度,超过这个度,物极必反。目前许多家庭都为小孩吃饭问题伤脑筋,不是担心没得吃,而是担心他不吃。
不说别人,就说我家小孙子。令人烦心的事就是吃饭。家里零食太多,随时拿出来吃,到吃饭时,他没食欲,抗拒吃饭,矛盾就产生了。我常想:吃饭是人的本能,吃喝玩乐,吃摆在第一位,吃饭成了家长烦心事,成了孩子负担,不合常理。
我的饮食习惯是孩童养成的,保留至今。我不太吃零食,看重一天三餐,到点吃饭,周围人看我吃饭都说:看老邓吃饭特别香。
有个传说,讲一个国王过着极尽奢华生活,吃遍山珍海味,感觉饮食无味。他问大臣:天下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找来给朕尝尝。大臣们面面相觑,不敢出声。有位大臣斗胆说:启禀大王,我打听到有种最好吃的食物,要去产地品尝。大王说:只要好吃,再远朕也愿意。
第二天早晨,大臣带着大王,浩浩荡荡驾车前往。走哇走哇,直到下午赶到一家偏远农舍,大王饿得饥肠辘辘,大臣献上三菜:青椒豆豉炒藕丁、家乡豆腐、清炒紫茄,外加锅巴粥。这些农家菜平时进不了皇宫,大王吃得津津有味,连声说:“名不虚传,好吃好吃。”下令带回御膳房,还重奖大臣。
这个民间传说不知真假,但说明一个问题:吃饭乃人之本能,饿了吃什么都香。开水泡饭外加豆腐乳,是我儿时早餐,至今依然喜欢。最近有部火爆电视剧《繁花》,剧中宝总出入宴席,吃遍山珍海味,私底下最爱的却是开水泡饭,我深有同感。
孩童喜欢打乒乓球,家里找块门板,架在长凳上就是球台,找根棍子架在砖上就是球网,大家轮番上阵比赛,开心得不得了。
孩童模仿力很强,用几个凳子围个小圈圈,把家里小玩具,瓶瓶罐罐当商品,模仿营业员叫卖声。邻居孩童也纷纷搭建自己“小商店”,暗地较劲,看谁店大,看谁商品多,有时互扮顾客,到“商店”购物,小伙伴非常投入,不亦乐乎。
每到夏天,我们喜欢玩蝈蝈,那时街头巷尾有卖,装在篾编的小笼里,一毛钱一只。蝈蝈叫起来特别悦耳,挂在门上精心喂养。有时放它出来玩,惊讶的是:蝈蝈逃跑,挣断一条腿也不在乎。
每逢夏天,九江酷暑难熬,西瓜成了人们的最爱。家里买个瓜,孩子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没冰箱,离家几百米有口井,井水较凉,我们去打水,把西瓜浸在水里降温,眼巴巴等着夜晚开吃。切瓜时在瓜头开个口,用勺子把瓜馕掏出,家人每人一碗。吃完后,瓜皮舍不得丢,在瓜口两端钻个小洞,用绳子系住挂在棍上,再把蜡烛点燃放进去,就成一只西瓜灯笼,还在瓜皮刻上“福”字,既好看,又增加亮度,一群孩童提着灯笼,从这家走到那家,可以闹腾一夜。
有段时间流行养蚕,有人给我一张蚕卵,回家找个纸盒,用棉花把蚕卵包起来。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蚕卵孵出没有。蚕宝宝出来那天,高兴得手舞足蹈。余下事是找桑叶喂蚕,每天观察蚕宝宝。这个过程较长,小蚕慢慢长大,食量也大,有时找不到桑叶,比自己没饭吃还着急,就到处找桑树。一点点看着小蚕由黑变灰,由灰变白,由白变通透。最后搭架作茧。有人从茧找出丝头,缠在笔筒上玩,但我没耐心,从未找到过。后来蚕蛾破茧而出,在纸上产卵,完成使命。
孩童养蚕没任何经济价值,只享受这个过程,看着蚕宝宝在自己喂养下一天天长大,经历蚕卵到蚕蛾产子全过程,体会多多,收获多多。
儿时也玩蟋蟀,最难的是抓蟋蟀。一到夜晚,巷子里常听见蟋蟀叫。它躲在墙角里,石头缝里,我们打着手电筒循声去抓,蟋蟀很机灵,很难抓到。玩蟋蟀的乐趣是看其打斗。蟋蟀好斗,把两只蟋蟀放进瓷缸里,马上互相追着撕咬,厉害的蟋蟀会把对方咬得遍体鳞伤,甚至咬下一条腿。胜者得意鸣叫,败者一声不吭,胜者主人喜形于色,败者主人灰头土脸,旁观者则拍手称快。
有时没有什么玩,蹲在墙角玩蚂蚁。我们找一粒米饭,放在蚂蚁必经路上,有蚂蚁发现了,停留观察一下,返回报告。只见它进入一个小墙洞。随即,一大群蚂蚁从洞口出来,排着队直奔饭粒。然后,十几只蚂蚁抬着饭粒,前呼后拥地凯旋,把饭粒运回小墙洞。我们惊讶地发现:蚂蚁是一群团结互助、有组织、有纪律的群居小动物,它们有头目,有分工,有合作,出行排成一条直线,缓缓前行,从不插队。此后,我们对蚂蚁刮目相看,再也不故意伤害它们。
此外,我们还玩过打三角(把吃完的香烟盒折成三角形,在地上互相拍,谁用自己三角把对方的三角拍到翻个面,三角就是你的了),飘画片(市面上有卖那种印有头像的画片,在墙上画一条线,每人把自己画片从这条线往下飘,谁飘得远,对方的画片就是你的),还有下象棋、五子棋、弹子棋等等。
冬季天冷,孩童穿得臃肿,又没什么道具,就玩斗飞机。游戏很简单,每人把自己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膝盖上,变成单腿在地上蹦跳,然后去撞击对方,把对方撞倒即为胜。可以两人对撞,也可以多人互撞。这个游戏能抗寒取暖,穿得厚,倒地也不会造成伤害,大家嘻嘻哈哈取乐而已。
俗话说“小孩盼过年,大人盼发钱”。我的孩童时代,物资紧张,工资偏低,大人要养家糊口,眼睁睁等着发放工资;小孩平日很少吃肉,过年可以大鱼大肉,饱餐几天,还能穿新衣,收红包,眼巴巴盼着春节早日到来。
那时大年三十没有春晚,男孩喜欢放鞭炮,用积攒的钱买挂鞭炮。用剪刀小心翼翼将成挂的鞭炮拆成单个,口袋装得满满的,吃完年夜饭,点根香,就迫不及待上街。市民几乎倾城而出,九江大中路、环城路、滨江路全是游龙,每条龙前有人手舞绣球,引着游龙腾跃翻滚。这些游龙有市区各单位组织,也有市郊农村来的。游龙路过商店门口,店主放鞭炮迎接,游龙就在店门前舞起来。舞到激烈时,舞者情不自禁发出“喔喔”叫声,观者发出“啊啊”喝彩声,不时还有人投进燃放的鞭炮助兴,气氛异常热烈!
游龙后面是彩龙船,一只装扮喜庆的布扎龙船,里面有位漂亮姑娘扮渔女,扶船的是位老船夫,拿着桨,边摇船边唱小调,有时渔女与船夫对唱。大都是祈福、祝愿、喜庆、调情内容,引得观众阵阵笑声、掌声及鞭炮声。
彩龙船后面是高跷队,一群穿着各式戏服的人踩着高跷,扮演百姓喜爱的角色,中间穿插“蚌壳精”,人躲在蚌壳里,一张一合,颇有情趣。
高跷队后面有个小丑,小个子,白鼻子,手拿破蒲扇,做各种滑稽动作,跟着队伍跑动打扇。小孩特别喜欢小丑,追逐逗弄,拍手叫好。这些九江传统民俗,从大年三十直玩到正月十五,深受市民欢迎。
我们这些孩童,哪里热闹往哪里跑,最喜欢干的就是用鞭炮炸龙头。龙头很重,舞龙头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龙头一刻不停地左右摆动,我们扔的小鞭炮根本近不了龙身。后来我们让鞭炮在龙口位置临空爆炸,达到这种效果,真不容易。一要把控点鞭炮时间,二要扔准鞭炮的位置,十次能有一次在龙口炸开,就非常不错了。
人到古稀之年,回忆孩童生活,既有恍如隔世的朦胧,也有亲切温馨的留恋。人都是从孩童走过来的,逝去时光不能再来,回忆之余,不免有点莫名惆怅。
我的孩童,那苦涩甜蜜的岁月!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王文婧
责编:刘芸
审核:姜月平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
赣公网安备36040302000178号